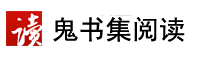第15节
“啊,摔死了?”满仓一惊,呼呼地喘着粗气问,然后探腰急向山坡下望去。
山坡下,暮色已拉开一张深不可测的大网,宛如一个巨大的麻袋,正向上张开着一张怪嘴似的黑幽幽的袋口。
“有人吗?有人吗?……”满仓两手在嘴边拢成一个喇叭状,对着黑黢黢的下面连声喊着,山林里便荡起一浪接着一浪的回声: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没有人回答。
幽深的山坡下,先是死一般沉寂。少顷,才听到一声**,弱如虫鸣地,仿佛从遥远的地狱传来……
第五十章 大梦终醒来
巧珍和巧巧得救了。
被巧珍撞下山崖的汉子也很快被救了上来。汉子伤得并不重,只是摔断了两根肋骨。汉子说,他只是一个靠采山过日子的光棍,因从未碰过女人,那天在山上碰到巧珍才起了歹意,至于巧珍娘儿俩是怎样到的山上,他真的不知道……
可满仓知道,他从父亲躲闪的目光和母亲的闪烁其词中看到了父亲的心虚和母亲的不安。在他的心中,真相,已经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了”。可他还是选择了沉默。毕竟,那是自己的父母,他不想让他们因此惹上牢狱之灾。他只有望着惊魂未定的巧珍母女,一遍遍告诉自己,今后一定要亲自保护这对母女,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
巧珍在经历了这件事后,突然变得少言寡语。她较过去不仅又减少了许多的哭闹,而且每天看着满仓忙忙碌碌地上下班,忙忙碌碌地照顾宽宽、巧巧和自己,眼里竟会泛出些许温柔和泪光。这让满仓很知足,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列火车,在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的一段隧道后,终于见到了光明,日子总算有了盼头。
“这看事先生说得还真准,巧珍跟了我以后,真的好多了。看来我和巧珍也真是天定的缘分啊!”他这样想。
满仓没有想到的是,巧珍的病,其实已经痊愈了。
原来,和满仓结婚后,满仓的细心照顾,已让巧珍的病情慢慢有了好转,意识和记忆都有了断断续续的复苏。那天在山林里的突然惊吓,又宛如一针强心剂,彻底激活和纠正了她原本就已经在慢慢复原的神经。
可是,痊愈后的巧珍,并不想急于说话,她每天陷于沉默之中,其实是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后的生活,她该何去何从。
巧珍足足想了一个月,当村里村外的丁香花开得灿烂如霞的时候,一个早晨,她推开窗户,迎接着清爽明媚的晨光,眺望着群山如黛的远方,突然感觉自己就像挺立在一个正在扬帆远航的船头,牛村和关于牛村的一切都被她远远地甩在身后了。
那一刻,巧珍心里突然纯净得像竹林里涌进了清风,她觉得自己应该做出最后的决定了。
巧珍作出决定的时候,满仓正在上班。
这天,满仓下班后,发现屋里没了巧珍和巧巧。他喊了两声,没人回答。往常他这样喊,即使巧珍不吱声,巧巧也会奶声奶气地答应着从什么地方小兔子般蹦出来,今天是怎么了?
满仓觉得很奇怪,他四处看了看,发现茶几的杯子下压着一张纸,纸上放着两张百元人民币。他走过去拿起纸条,见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字条是巧珍写的:
“满仓,你好。自从那天你救我出密林后,我的病就已经好了。之所以不想让你知道,是不知道清醒后的我该如何去面对你我十年以后又走在一起的那份尴尬。
满仓,其实你我都明白,我们的心里也许还都珍藏着对方,可是,当年的一场误会,已注定了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的心境,尤其是山娃死后。
山娃对我很好。在我最绝望、最无路可走的时候是他娶了我,给了我一份曾经十分平静的生活。如今,他已经不在了,对于他的死,你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这责任不在法律的范畴内,但却在良心的词典里。所以,过去我已经对不起他了,现在更不可能用他的生命和鲜血来酿造我们的幸福,那样,对你我来说,也绝对不会是幸福。所以,我走了。宽宽是你的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待他,巧巧我带走了。
还有,这二百元钱是当年我上卫校时你送给我的,我一直带在身上,没舍得花,现在就物归原主吧!……。巧珍”
“巧珍!”满仓心里大喊一声,然后拔腿向外奔去。
满仓出门不远,就看到谢三娘手里捏着一封信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向他迎面走来。
原来谢三娘也刚看到巧珍留给她的信。“你说这孩子能死到哪去啊!”看到满仓手里也握着一封信,她彻底失望了,撩起宽大的袖口掩面大哭起来,“这好日子刚开头啊,你说你这苦命的傻孩子唉,怎么就偏跟福气过不去啊……”
满仓没有理会谢三娘,他拼命地向村外跑去,希望巧珍娘儿俩还没有走远。可他沿着村外那条明晃晃的大路追出了几里路,竞没有看到娘俩儿一定点儿的影子……
满仓的脚步随着内心的绝望渐渐放慢下来,最后终于气喘吁吁地停下来。他手里捏着那二百元钱,呆呆地站立在灼热的阳光中,两串泪水像两道决堤的山洪,冲破他曾经自认坚强的心理堤坝,奔流而下……
是啊,在这之前,他还以为自己与巧珍的再次结合完全是为了挽救巧珍的命运,是自己应该承担的一种责任。可当他再次看到那两张百元钞票时,他才明白,自己的内心其实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巧珍的爱,那种灵魂遇到灵魂的感觉,原来一直隐藏在他内心的深处。此时,他再次想起那次在巧珍家看到疯癫中的巧珍从他手中抢过这两张钞票时的情景,心痛得无法抑制,他实在想象不出巧珍是怎样在一次次磨难之中做到完整无缺地保存着这两张钞票的?那一定是把它视之为了与生命的同等重要,不然何以在她痛苦时、疯癫时、遇难时都能够做到如此的小心、如此的在意、如此的珍藏?
那不是两张钞票,是巧珍对自己一直不曾离去的爱啊!
想到这儿,满仓觉得自己的生命也被巧珍带走了一半,他不禁难过地对着远方大喊:“巧珍,你在哪儿啊——”
此时,在离牛村已二百多里的一辆客车上,坐在窗边的巧珍正看着路边飞速疾退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泪流满面。
“妈妈,你怎么哭了?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坐在身边的巧巧看着妈妈问。
巧珍急忙擦开泪水,扭头笑着对巧巧说:“妈妈没哭,妈妈要带你啊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太好了,太好了!”巧巧高兴地拍着巴掌,又突然仰起圆溜溜的小脸,小鸟儿般看着巧珍问,“可是妈妈,那儿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
是啊,那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呢?巧珍也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已经大梦醒来,从这一刻起,她必须要学会坚强地自己掌握命运了。
第五十一章 宽宽的复苏
转眼,巧珍出走已半年了。半年中,冬天就像一个串门的常客,来了又走了。满仓也候鸟般来来回回去省城和南方一些地方找了三回,可巧珍就好像突然在人间蒸发了一般,就是没有一点音讯。
为了排解心中的烦闷和对巧珍的思念,满仓就像一头被注射了兴奋剂的公牛,每天不停地奔走于办公室和养牛户之间。尤其眼下是春耕季节,村里的牛群总会和路上来来往往的农用机车频繁碰面,安全问题站在了众多工作的最显眼位置,所以他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问题,必要时还要亲自逐门逐户地进行宣传教育。
这天,转完所有的养牛户,已是傍晚时分,满仓拖着酸痛的腿向家走着,疲惫的身影在夕阳中拉得老长。可他越来越喜欢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时候,他可以让后反劲儿的疲累肆意地侵占他的身体和思维,让他没有精力和心思去想念巧珍;这样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晚归的耕牛,披着晚霞的彩衣,一路慢慢地走来,慢慢地享受着这暂时属于自己的时光。这个时候,他可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包括那个没有了巧珍的不再完整的家。因为,他太累了,这个时候,他希望自己就是天上的一抹云,只需慢慢地走着静静地徜徉即可,
满仓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家门口。他的心又开始堵了起来。他轻叹一口气,伸手正要轻推家门,突然感到“嗖”的一声,好像有个影子从仓库房头一闪即逝。他先是一愣,接着三两步追过去。可仓库后,但见荒草摇曳,一片夕阳掩映的凄凉景色,哪里有什么影子?
许是自己太累了,眼花了。满仓这样想着,推开了家门。
屋里,静静的,没有一丝声音。再向里走,却见谢三娘蜷缩在床角,浑身战栗着。
巧珍出走后,满仓除了自己出去寻找过,还一直托人帮忙打探着。前两天,理疗师说他在省城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帮上忙,满仓便求他回省城安排一下。理疗师走后,照看宽宽的事自然落在了谢三娘身上。
“怎么了?”看到谢三娘的样子,满仓满心惊讶地问。
“有鬼……”谢三娘一动不动,双手死死抱在眼前。在满仓眼中,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还是头一次表现得如此不堪。
满仓四周看了看,边说:“哪有?”边伸手去扶已吓得软成一团的谢三娘。
“是真的,一个女鬼,先是在屋后哭,后来又站在窗下哭,好瘆人啊!”谢三娘边战战兢兢地起来,边描绘着,额头和两团高高的颧骨上因恐惧挂满了细密的汗珠。
满仓想想刚才似有非有的影子,心里也有些发毛,但不管怎样,总不能在谢三娘面前丢丑。想到这儿,他以一个无畏者的口气下了定论:“哪有鬼,一定是你照看宽宽太累了,出现了幻觉。”
满仓的话音刚落,一个稚嫩的声音突然脆生生地在他耳畔响起。“是真的有鬼,我也听到了!”
满仓一愣,惊讶地抬起头。这一抬头,他的嘴竞也跟着大张起来。他不禁扭头看看谢三娘,只见谢三娘也正眼光直勾勾地望向床上,整个人目瞪口呆:床上,已昏睡了近两年的宽宽不知何时奇迹般地坐了起来,正望着他认真地说:“我真的听到鬼哭了,是个女的。”
“儿子!”满仓愣怔了半天,终于回过味儿来,他激动地扑过去,猛地把宽宽拥入怀中,泪水扑簌而下。谢三娘也一口一个“外孙”地叫着拥过来。
宽宽被满仓抱得透不过气来,他拼命挣脱了满仓,一双黑黝黝的大眼睛望着满仓问:“你是我爸爸吗?”
满仓一时语噎,不知如何回答。
“你是我爸爸吗?”宽宽再次问道,纯净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和渴望。
满仓不忍再沉默,使劲点着头说:“是,我是你爸爸,儿子。”
“那就好,爸爸是这个样子,我在梦中怎么也想不起来。”宽宽笑了,一副很满足的样子。虽然他看起来还很虚弱,但这丝毫不影响笑容绽放在他脸上的灿烂和光辉。
满仓和谢三娘心里同时一惊:莫非这孩子的脑子留下了什么后遗症?出了什么问题?
满仓想了想,翻出家里的相册,指着里面巧珍和巧巧的照片问宽宽:“这是谁,宽宽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是妈妈和妹妹。”宽宽很自信地回答,接着又用手一指谢三娘道,“这是姥姥!”
“那,宽宽还记得谁?”满仓急切地问。
宽宽摇摇头,有些奇怪地望着满仓迫不及待的样子说:“不记得了。”
满仓和谢三娘不禁面面相觑:看样子,这孩子谁都记得,就是把山娃忘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几天后,理疗师回来了,解释说:人的大脑有一种自我保护功能,如果一个人或一件事会让一个人伤心痛苦到要发疯或自我毁灭的时候,大脑的这个功能就会自动启用,在这个人的记忆中屏蔽掉这个人或这件事。山娃的被捕和对宽宽的伤害,已经严重刺痛了宽宽,所以宽宽的大脑已经把山娃屏蔽掉了。当然,这种事情不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发生了,可在宽宽身上发生,实在是上天对满仓和宽宽父子的一种眷顾。
理疗师的话让满仓得到了莫大欣慰,不管怎么说,在宽宽的心中,今后毕竟只有自己这一个父亲,更重要的是,自己确确实实是给了宽宽生命的亲生父亲。
宽宽的苏醒,让满仓一时间竞忘掉了那天岳母和宽宽听到女鬼哭泣的事情,不,确切地说,是忘乎所以的欣喜冲淡了来自鬼情的忐忑。他握着巧珍留给他的那两张纸币,看着奇迹般恢复的宽宽,想,巧珍走了,可宽宽却清醒了,老天对他,还算是眷顾的。
可稍有闲暇时,满仓还会在心里问:那个闪过的影子,到底是谁呢?是人还是鬼呢?
第五十二章 谢三娘辞世
“爸爸,我姥姥病了,说是肚子疼。”宽宽苏醒的第七天上午,满仓正在办公室写份材料,宽宽急急忙忙地跑进来说。
“疼得厉害吗?”满仓问。
“厉害,疼得都直不起腰来了,直叫唤。”
满仓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拿起电话向农场医院要了辆救护车,然后急三火四地和宽宽一起向巧珍家老房子跑去。自从宽宽苏醒后,谢三娘就搬回了巧珍以前的家。
满仓赶到时,谢三娘正捂着腹部跪在床边,头上汗珠直滚。
二十分钟后,救护车鸣着响笛接谢三娘到了农场医院。可各项检查都做完之后,医生的结论却出乎人的意料:没有查出任何毛病。
可谢三娘真的是疼得死去活来呀!这真是太奇怪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满仓又带着谢三娘去了县医院、省医院,结果都被医生沉重而无声的摇头和叹息遣回。
其实在满仓第三次寻找巧珍无望而归后,病魔之手就已经伸向了谢三娘,且像挖墙脚一般,一点一点摧毁着谢三娘本就日渐衰老了的生命根基。对此,谢三娘并非毫无感知,只是,仿佛跟谁赌气似的,她隐忍着丧父又失女的巨大悲痛,拼命照顾着宽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却只字不提。
她自己知道,她只能用此方式来向自己丢失的女儿赎罪了。
这是谢三娘还能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如今,宽宽苏醒了,并且日渐一日地强壮起来。谢三娘便宛如完成了一项神圣使命似的,心中以此为支撑的人生构架轰然倒塌了。这个强势了大半辈子的女人,终于没有抵得过一次次接踵而至的变故的打击,而毫无选择地摔倒在了病魔的怀中,且很快从虚弱走向了奄奄一息。
谢三娘的状况,让心里对她一直充满了厌恶和怨恨的满仓也不得不同情起她来。他知道医生的摇头和叹息意味着什么。不管怎么样,毕竟是巧珍的母亲、宽宽的姥姥。他这样想着,便不顾工作多么繁忙,坚持一日三餐地照顾着谢三娘。
谢三娘病得很奇怪,虽然在几家医院都没有检查出毛病,可从医院回来后,疼痛竞奇迹般地消失了。这让满仓颇为欣慰,他刚在心里念了句“阿弥陀佛”,却突然发现,谢三娘表情奇怪地瘫坐在了地上,任他怎么扶也再也扶不起来。
谢三娘瘫了,满仓只好把她又接回了自己家照顾。
不再疼痛了的、瘫痪了的谢三娘突然恋上了说话。她每天早晨睁开眼就开始不停地说话,好像说话是她的一项工作似的。她说话的神态很自然,好像身边有很多人在跟她唠嗑。她唠的嗑也很广泛,天南的海北的,过去的现在的,村东的村西的,无所不及。她说话的时候很精神,看不出有丝毫病态,可稍微停下来一小会儿,就会气若游丝,好像生命的秋千忽然间悠荡到了死亡的边缘。
每每这时,满仓就害怕地对谢三娘说:“妈,您怎么不说话了?怎么不唠嗑了?”
谢三娘就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他们都走了,不跟我唠了。”
满仓不知道谢三娘口中的“他们”是谁,此时,他只需要谢三娘状态赶紧好起来,跟谁唠嗑并不打紧。他就说:“那您跟我唠呀,唠什么都行。”
“你,不行。”谢三娘说,“只有他们才行。”
“为什么只有他们才行?他们都是谁呀?”满仓问,其实他只是想让谢三娘继续说话而已。
“他们都是些死了的人,可现在天天都回来看我。”谢三娘说着,便念叨起了那些死人的名字。
满仓的心就“咯噔”一下子,他知道这不是好兆头。他下意识地四周看了看,心有余悸地对谢三娘说,“妈,以后您别再跟他们唠嗑了,他们若来你就撵他们走。没事时我陪您唠嗑。”
这个时候,谢三娘的思维是清醒的,她知道满仓的用心。这些年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波折,她也彻底改变了对满仓的看法,对自己当年的“棒打鸳鸯”后悔不已。这会儿看女儿都丢了,女婿对自己还这么不计前嫌地孝敬着,更是羞愧难当。她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满仓说:“满仓啊,别再为我受累了。妈过去对不住你,现在你这么伺候妈,妈心里有愧啊!”
满仓看着岳母,看着这个过去壮实得像头牛,吵起架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的女人,如今却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日渐变小的身躯躺在床上,床便像一日日在加宽似的。这让满仓心里隐掩不住地发酸,他说:“妈,您别想那么多,您是巧珍的妈、宽宽的姥姥,我伺候您还不是应该的?”
谢三娘便深深地叹口气,转过头去悄悄地流着眼泪。
两个月后,春天像一双大脚刷刷走过的一个傍晚,夜色吞没了黄昏最后一抹剪影,牛村在突然烘热的晚风中并不急着睡去,而是微微喘息着坚持把人牛共振的交响曲奏得更加响亮而热烈。
可远在村头的满仓家,此刻,却是异常的安静,安静得听得见一根针落地的声响。
这个傍晚,饱受了生活磨难的谢三娘终于挨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是一幅与此时仓库身后的村庄极其格格不入的凄凉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