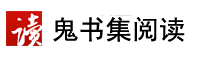第14节
可人鬼相约,这又怎么可能呢?所以让自己娶巧珍是万万不能的。想到这儿,满仓黑暗中的脸上显出一丝无奈的苦笑。
可他又真的能放弃巧珍吗?他反问自己。
像走路从一个拐角转到了另一个拐角,满仓的感觉是刚走过一堵墙又遇上了一堵墙。他知道他的思维又开始发生了摇荡。果然,刚才侧重于秀秀那边的天平,此时随着他的自问,又开始了向巧珍那边的倾斜。
这真的是一件令他很无奈的事情,他越是像驱赶蚊虫那样驱赶着这要命的无法掌控的思维,这种思维便越像站在栏外的一头晚归的牧牛,倔强地以角抵栏,哞哞地叫着要进来。
关于他和巧珍的记忆,就在这时从他迟疑着的不知是应该打开还是应该关闭的窗口潮水般涌进来,且从青涩的初恋开始一泻千里,甜蜜、忧伤、怜惜等诸多感觉令他无法招架、无法逃脱、无法不去面对。这个时候,他更多想到的是“责任”二字。
他知道,只有“责任”二字,才是他迎娶巧珍的最有力砝码。因为这“责任”,不仅仅是对巧珍,还有宽宽。
他终于决定下来要娶巧珍。
秀秀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一定会理解我的苦衷的。他这样安慰自己。
这样想着,分析着,他的心情便开始安宁下来。他闭上眼睛,想趁着黎明到来之前睡上一会儿,可也许是刚才再次提到了“秀秀”两个字的缘故,这两个字竞像一根线头,引得他又情不自禁地摁着有关秀秀的记忆的线团使劲地扯起来,且越扯越多,越扯越沉,这就使得刚刚倾向于巧珍的天平又很快地悠荡回来……
满仓思想的天平就这样在秀秀和巧珍之间来回地摆动着,完全找不到了平衡点。他仿佛处在风口的一条船,在经过了一次次左突右冲后,终于近乎绝望地渴盼着一个人能来为自己进行一次决定命运的推波助澜。
铁生就是这个关口的这个人!他的推波助澜方式很简单,只是一个电话而已。
满仓接到父亲电话时,是上午九点多钟,他正坐在办公室无精打采地写一份关于牛村规划的材料。昨夜的整宿未眠,令他的眼皮就像被粘住了一般,沉重得难以睁开。
父亲的话很直接,大意是,已经对不住了秀秀,就不要再对不住巧珍和宽宽,咱,总得为活着的人着想吧!何况,巧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也是跟你有直接关系的,作为男人,总要有担当才对。再说,秀秀是个难得的明白人,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绝不会怪你和巧珍的。
父亲的语气少有的宽厚、缓慢和温和,却像一把手术刀快速剔除了满仓脑中累赘般多余的思维,他的心随之豁然开朗,立马坚定了迎娶巧珍为妻的决心。
满仓知道,要娶巧珍为妻,必须要过了秀秀的母亲申敏这一关才行。所以趁星期天,他早早赶去了申敏家,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向岳父岳母交代了个明白,并保证即使娶了巧珍,他仍会一如既往地奉养申敏二老,决不让他们觉得晚年孤单。
满仓觉得自己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足够感动申敏二老。可没想到申敏听完仍然火冒三丈,她失去理智般对满仓破口大骂,发疯似地把满仓和拿来的礼品一起推出了门外,同时还扔出了一句锋利无比的狠话:
“只要娶了巧珍,咱们从此就是仇人!”
申家的大门“砰”地一声关上了,满仓的心也再次陷入了为难之中。他站在嗖嗖的冷风中,像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不知该怎样去面对自己和巧珍的这段难续的前缘……
第四十七章 夫妻之大战
把满仓撵走后,申敏像枚憋了许久的炸弹,彻底爆炸了。怎么,不是说只是帮帮吗?怎么突然又要结婚了!这,这也太不顾我们申家的感受了!她走马灯似地在屋里一圈圈走着,情绪失控地大喊大叫着,然后一把推开挡在门口企图阻拦她的丈夫,一路哭泣着跑去哥哥家告状。尽管她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哥哥也许并不是她的救世主,可除了哥哥,她还能去找谁呢?
可走进哥哥家,申敏愣住了。
屋里,哥哥正铁青着脸站在客厅中间,脚下铺满了烟头。嫂子流着泪坐在沙发上,跟前的地上乱七八糟的扔满了东西,尤其惹眼的,是几只晶莹剔透的玻璃杯,它们带着形状各异的摔伤,静静地躺在角落里,宛如几只受伤的眼睛,委屈地瞅着身边碎心一般的玻璃碎片黯然神伤。
显然,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浓重的火药味儿还没有完全散去。这可是申敏从来没有见过的,因为在她的心目中,哥哥嫂子一直是恩恩爱爱、和和睦睦的,今儿个是怎么了?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声音有些发抖地问“你们这是……?”
“没事,我和你嫂子正谈点事,你若没什么要紧事,就先回去吧。”申志强一屁股坐到离冷月两米之遥的另一张沙发上,双手痛苦地拄着头揉搓着,说。
“干嘛让她回去!”申志强的话音还没落地,冷月就呼地从沙发上站起,一个箭步冲过来拦住申敏,咄咄逼人地对申志强说“你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连亲妹妹都不敢见了?有本事把你做的那些丑事说出来给你妹妹听听!”说着扭头又对申敏说,“申敏,你给评评理!你知道吗,你哥长本事了,本事大了!他在外面养了女人,而且还不止一个!”她的双唇快速地翕合着,像一个仇恨满腔的机枪口突地射出了一串又一串子弹,在说到‘一个’两字时还特意加重了语气,以示强调。
申敏大吃了一惊,嘴张得圆圆的,显然是一个没有吐出口的“啊”字的口型。自从那天嫂子问她哥哥过去定没定过亲起,她就隐隐约约感觉到哥哥嫂子之间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却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又这么严重。
申敏从没见过嫂子如此激动,她边轻轻地拍着嫂子的肩膀安慰着,边从嫂子极其委屈的又哭又说中,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自从发现了丈夫和倩姨的奸情后,冷月就拒绝和丈夫做任何形式的交流,认为事实胜过雄辩。两个人就这样陷入了僵局。原本想着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的,可一天晚上,正在失眠的冷月再一次听到了丈夫的梦呓:“梅梅,我好想你,你到底在哪儿呀?你原谅我,不要不理我,梅梅,你别走……”
梅梅?丈夫的梦呓提醒了冷月。她突然想起,丈夫已经不是一次在梦中呼唤这个名字了,自己原本要找出的分明是这个梅梅,不曾想半路上却杀出个倩姨来。这些天,光寻思着倩姨的事了,却忘了这个梅梅!
那么梅梅又是哪一个呢?难道丈夫在外养的女人还不仅仅倩姨一个?想到这儿,冷月气愤得发了疯,她仿佛突然从一只忍辱负重的羔羊变成了凶猛剽悍的野兽,掀桌子般掀起睡梦中的申志强厉声质问。
申志强知道自己又闯了祸,可他突然不想再解释。这些日子,他使尽浑身解数乞求着冷月的原谅,但得到的仍是她不依不饶的冷漠和讥讽。这让他感到了失望和疲倦。同时因为看到了妻子刻薄泼辣的一面,他竟对妻子滋生出了从未有过的陌生和厌烦,这让他先前对妻子的隐隐愧疚也就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所以,无论是关于倩姨还是梅梅,他都不想再做什么解释,任凭冷月变着法儿地吵闹。
于是,申志强翻了个身又假装睡去了,任凭冷月把东西雨点般砸在他裹着被子的身上,他都缄默如铁,不予理睬。
申志强的漠视让冷月气愤难当又无计可施。离婚吧,这让她的面子实在不允许。不离吧,难道自己就该吃这哑巴亏受这窝囊气吗?思来想去,最后,自觉无路可走的她干脆玩起了与其他俗女人同样的伎俩:一哭二闹三上吊。
听完嫂子的哭诉,申敏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想说哥哥两句,却看到哥哥脸铁青着,眼圈黑黑的,想这几日肯定被嫂子折腾得够呛,心里实在有些心疼。说嫂子两句吧,又实在没有理由,都被抓现行了,这事明摆着是哥哥理亏在先了。
申敏就这样左右为难地站了一会儿。过去,她一直觉得哥嫂的婚姻是完美、最无可挑剔的,可眼前发生的一切,宛如突然拉开的幕布,让她看到了里面每个演员最真实也是最虚伪最残酷的道具下的面容。
“唉,哥哥竟然会**,嫂子原来也会这么泼。人啊,原来就像一本书,无论封皮多么精美,都不要轻易相信里面的内容啊……”申敏在心里感慨着,觉得自己一时间也帮不上哥哥嫂子什么忙,再说遇上这种情况她也无法再说出自己的来意,只好草草地又安慰了冷月两句,然后像一条蛇似的悄无声息地隐退了。
申敏走到屋外,发现来时还响晴的天此时竟从西北方漫上了几片黑云。黑云越聚越多,最后层层叠叠的,像一只只笨重的结伴而行的怪兽在爬,爬到中天时,天就黑压压的变得很低,压得人心沉颠颠的透不过气来。
“要变天了!”申敏想着的当口,头顶便有一阵风斜斜地吹来,像夹着沙,打在脸上生疼。接着,便有几片雪花清爽爽地飘落,探路一般,后面很快跟来了北风裹挟着的白茫茫一片的冬雪大军。
申敏就在这风雪突来的黄昏里,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申家,似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第四十八章 铁生的阴谋
满仓在被申敏第六次赶出家门后,毅然和巧珍简单地举行了婚礼。为了添些喜庆、祛除晦气,满仓找来泥瓦匠,又为仓库新居换了套新衣,想以此再为仓库冲冲喜。
婚后的日子,就像一条刚刚驶出港口的船,沿着计划的航线风平浪静地行驶着。在理疗师和满仓的悉心关照下,宽宽和巧珍的病情都有了好转。宽宽手脚微动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巧珍虽还痴痴呆呆的,却平静安然了许多。这一切都让满仓的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心想厄运终于要过去了。
可有一个人却觉得这厄运的尾巴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他决定要帮着满仓剪掉这条尾巴。
这人便是满仓的父亲:铁生。
铁生今年不到七十岁,除了腿脚残疾外,身体其他状况还算不错。铁生虽然当过干部,可觉悟实在不怎么高,而且生就的倔脾气、冷心肠,所以老早便得一绰号:死铁。
满仓和巧珍结婚后,看着宽宽的病一天天好转,铁生无时无刻不在为孙子的重生而高兴,同时也在为儿子盘算着怎样摆脱掉疯媳妇巧珍。
只要没有了疯媳妇的拖累,儿子的倒霉日子就真的过去了!他想。
铁生就这样盘算着,从寒冬腊月一直盘算到了来年的仲夏。
一天,他拄着拐,在绿意盎然的院子里一瘸一拐地转了几圈后,突然回到屋翻了翻墙上的日历,然后神秘地趴在老伴耳边嘀咕了半天。老伴铁嫂听后面色大变,惊骇地问他:“当初不是你劝儿子娶巧珍的吗?怎么这会儿又……”
“当初不是为了明正言顺地要回孙子嘛!这回孙子回来了,难不成还真让儿子跟个疯女人过一辈子?”铁生咣咣地在地上狠顿了几下拐杖,白了老伴一眼说,“亏你还是个当娘的。”
“可这毕竟是……”铁嫂继续坚持说。
“行了!”铁生不耐烦地打断铁嫂的话,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事就这么定了,有事我担着!”
铁嫂知道老伴的死硬脾气,不再吱声了,可脸上却布满了焦虑与慌乱。
三天后,是农场场部大集的日子。这天一大早,铁生便打电话让满仓把巧珍和巧巧送过来,说要让老伴陪她去集上逛逛,散散心,病兴许会好得快一些。
满仓很高兴,觉得父亲真的是越来越通情达理善解人意了,便骑上摩托车早早把巧珍和巧巧送到了父母家。
满仓走后,铁生咬着铁嫂的耳朵把前两天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
铁嫂木木地听后,看了铁生一眼,嘴张了几张,终于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但从她的表情看得出,她此时的心潮一定是惊涛拍岸般汹涌不止。
半个时辰后,估计大集上人上得差不多了,铁生便给铁嫂使了个眼色。铁嫂自从嫁给铁生那一天起,便受了铁生大半辈子的气,听了大半辈子的话,此时更知道拖不过,无奈便带着满脸难色毫不情愿地走到巧珍娘儿俩跟前,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巧珍呵,走,妈带你去赶集,行不?”
铁嫂人长得慈善,说话又柔软,这让正搂着巧巧坐在板凳上扒花生的巧珍感到了无比的亲近,她抬起头,天真地想了一下,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问:“那,宽宽呢?”
铁嫂顺杆爬地说:“宽宽在集上,正等着你呢?咱快走吧!”
巧珍眨巴眨巴眼睛,半信半疑地牵着巧巧的手跟铁嫂走了。
九点半钟的光景,集上人正多。可铁嫂领着巧珍娘儿俩并不往集上去,而是沿着场部边上的一条小道向一片山林走去。
路上行人很少,估计都去了集市。铁嫂这时才恍然明白铁生之所以让她这个钟点出来的原因,就是让更少的人看到铁嫂的行踪,以增加行动的保密性。“这个阴狠的老不死的东西!天生的就没长好心肠!唉,命苦哇!”她在心里恨恨地骂着铁生,同时感叹着跟在身旁的巧珍娘儿俩的悲苦命运。
铁嫂引着巧珍娘俩儿走得很快,生怕有人追来似的。这样不知走了多久,小道曲曲弯弯地越来越幽深,山林也越来越幽静,只听见三个人呼呼的喘息声。
铁嫂突然有些害怕起来。她停下脚步,前后左右看了看后对巧珍说:“巧珍,满仓和宽宽就在前面等你呢,快带巧巧去吧。妈走累了,坐这儿歇歇等你们。”
一听到满仓和宽宽的名字,巧珍立刻面呈喜色,拉着巧巧雀跃前去。
待一大一小两个背影倏忽转而不见,铁嫂急忙转身向来路落荒逃去。
话说满仓从场部回到牛村后,边在村里巡视着,边怀着一颗感激的心回想着父亲的一次次人性大改变。他想着想着,前方不远的树上突然扑愣愣地飞起两只乌鸦,“哇哇”地叫着在他头上盘旋。这让满仓脊背一凉,一种不好的感觉突然电流般直击全身。难道要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会有什么事呢?他有些不安地问着自己,并对身边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进行猜测着。
突然,满仓的心中突然飘过一片疑云:不对呀,按照父亲粗俗的性格,就是再改变,也不至于精细到专门领疯儿媳妇去赶集呀!没这个必要哇!满仓的心忽悠悠地沉了下去,越发觉得今天的事情,不,确切地说,是今天的父亲表现得实在很蹊跷。莫非……?他突然想起父亲的绰号“死铁“,心里一阵慌张。他来不及再多想,骑上摩托又重新向场部飞驰而去……
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半多钟,集上的行人较上午已经少了很多。满仓在集上转了一圈没有看到母亲和巧珍,便又旋风般赶到父母家。
推开门,便见父亲和母亲正相对而坐,父亲抽着闷烟,母亲的两眼红红的,显然刚刚哭过。
这场景,让满仓的心激伶伶打了一个冷颤,他感觉自己的预感似乎成真了。果然,母亲见他进来,突然放声大哭说:“满仓,妈对不起你呀,妈把巧珍娘儿俩弄丢了呀!集上人太多,一转眼,人就不见了呀!”
完了!满仓心里大叫着。这一刻,他紧张、激愤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把质疑的目光投向父亲。因为,他并不相信这是母亲的疏忽,这一切一定都是父亲搞的鬼!
满仓刀子般的目光让铁生的心着着实实地哆嗦了一下子,但他不愧于他“死铁”的绰号,短暂的哆嗦后,仍能深藏内心的慌乱,勇敢地抬起眼皮去迎接儿子怀疑、激愤、灼人的目光,等待着儿子即将爆发的严厉质问。
可满仓什么也没说,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他深深了解的父亲,转身冲出了大门。
第四十九章 密林中遇险
幽深密集的树林里,一条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上徘徊着巧珍娘儿俩。从早上的八、九点到下午的三点多钟,娘儿俩已在密林里转悠了七个多钟头,饥饿和疲惫早已像两只邪恶的手,牢牢地卡在她们的脖子上,令她们虚弱得喘不上气来。
密林虽然靠近城郊,可却是当年建场时留下的唯一一片原始森林,多年来由于频繁采山的缘故,密林深处山道纵横,宛如一条条爬行在林中的细蛇,或直行、或盘环、或交织,不深熟路径的人身在其中就如陷入迷宫一般。
巧珍领着巧巧就这样在密林中穿来穿去,不但没有见到满仓和宽宽的影子,就连来时的路口都不知遗失在了哪里。
不知不觉,太阳从东边移到头顶,又从头顶坠向了西山。
黄昏了,林中很快暗了下来。透过林间缝隙,夕阳的光束懒懒地照进来,像一支电量不足的手电筒,发射着有气无力的光束,为黄昏的林中铺满了星星点点、斑驳不一的夕照和暗影。
这些暗影随着夕阳的移动忽而变长、忽而变短,忽而直立、忽而潜伏,像一个个怪异的影子在巧珍和巧巧身旁忽隐忽现着。此时,各种莫名其妙的声响也开始在林中传荡开来,在暮色笼罩的沉寂的森林中,宛如一群刚刚醒来的鬼魅,忽远忽近、忽高忽低、忽喜忽怒地叽叽咕咕交谈着,阴瘆而惊悚。
巧珍感到一阵恐怖正在心头快速漫延。此时的她,似乎已完全明白,自己和巧巧,是被人给遗弃了。这从她突然已变得不再涣散的眼神便可看出。于是,一种母爱的本能令她紧紧地牵着巧巧的手,生怕一松开,巧巧就会被突然从天而降的怪物掳去似的。
“妈妈,我饿了,咱们的家到底在哪儿呀!”巧巧突然说,稚嫩而清晰的声音更加重了森林的幽静和巧珍心头的惊恐,她觉得这惊恐正让她原本混沌的思维变得清晰和逼真起来,她伸手一下捂住了巧珍的嘴,一双充满了焦虑和惊惧的眼睛急速地朝四处转动着。
“呵呵呵呵……”果然,随着一阵夜猫子般的笑声,一种低沉阴冷的声音从她身后随风飘了过来,“小丫头,饿了跟我走吧,保你吃个够!”
巧珍一惊,冷汗忽地从全身各个汗毛孔冒了出来。她寻声转身看去,只见微薄的暮色下,一个长相奇丑的背筐汉子正站在她们身后左侧,脸上堆着厚厚的猥琐的笑,在暮色笼罩的林间背景下,更像一只吃人的山怪。
巧珍“啊”地尖叫一声,拉着女儿本能地一步步向后退去。
汉子更加得意,边从肩上往下卸着背筐边说:“老天有眼啊,虽然今天没采到多少山货,可却得到了这么漂亮的小娘们儿,看来我的艳福不浅哪!”说着,伸出暮色中鹰隼般精瘦尖长的双手,一个饿虎扑食便向巧珍扑去。
“不要抢我的孩子!”巧珍尖叫一声。自从谢三娘用理疗师残害孩子的谎言吓唬巧珍后,巧珍的心里就被埋下了“抢孩子、害孩子”的悬念,碰到陌生人就觉得人家要抢自己的孩子,此时更是这样。所以,没等汉子近身,母爱的本能便已令她完全忘记了害怕,她没有坐等待毙,而是抢在汉子之前低头弯腰牛一般迎着汉子撞去。
巧珍这一撞是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又恰逢汉子的身后是一个陡得近乎直角的山坡,所以随着巧珍的猫腰前冲,汉子防不胜防,“啊“的一声长叫着向后仰去,顷刻间便没了踪影。只有几只被惊起的猫头鹰,扑愣愣地飞起又轻飘飘地落下,然后嘿嘿嘿地发出一阵咳嗽般的冷笑,像议论,像嘲笑、更像鄙视。
一切发生得那样突然,巧珍由于用力过猛,险些与汉子一起跌落山坡,亏得坡下一米处一棵老树颤悠悠地接住了她。巧珍抱住树干,惊恐地尖叫着救命,惹得上面的巧巧也跟着嚎啕大哭起来。
呼救和哭声惊雷般在密林的上空一阵阵滚过,惊得树丫间众多不知名的大鸟们叽叽嘎嘎地一阵飞起,像一个规模强大的机群,发怒似地在巧巧头上方一圈圈示威般盘旋着,吓得站在坡沿上拼命喊着妈妈的巧巧更加倍地发出了凄厉的哭喊声。
女儿的哭喊,像一把把飞掷的刀子,每一把都扎在巧珍的心上。她不知上面又发生了什么,便拼命摇撼着拦着她身体的老树,边摇边用已嘶哑了的喉咙喊出了聚集了生命所有底蕴的一句:“满仓——”
喊声尖锐而绝望,似乎在每一个树梢上都溅起了火花,精心而动魄。
“巧珍,不要怕!我来救你!”正慌乱间,一个黑影从远处边喊边急速而来,速度快得像一颗疾飞的子弹,瞬间便已奔至眼前。
是满仓。
原来,满仓寻遍了整个场部都没有见到巧珍,便一步步寻上了山,走到半山腰岔路口处,正不知该往何处时,忽然隐隐约约听到了巧珍娘儿俩的尖声哭叫,便十万火急地循声奔驰而来。
满仓找到一根木棍拽上巧珍。
“怎么样,伤着没有?”满仓急切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