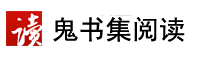第13节
女人收完衣服,刚要转身进屋,却突然看到了不远处正在呆呆地望着她的申志强。
四目相对,女人的轮廓在申志强眼中进一步清晰起来:肤白胜雪、身材匀称,杏核眼上的双眉轻轻蹙着,在眉宇间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疙瘩,像是裹着一团莫名的忧郁。好在女人生了一副嘴角月牙般上翘的乖巧嘴巴,这不仅大大减轻了她的年龄,还冲淡了那团忧郁。
这是一个气质高贵的漂亮女人,岁月的风霜虽在她眼角、额头留下了些许沧桑印记,却仍掩不住她姣好的容颜和绰约的风姿!
申志强的心狂跳起来,原来,倩姨和照片上的那张面孔竟真的那样的神似,甚至可以说是一张面孔的两个时光版,除了眼前这张眉宇间的那团忧郁!
是她复活了吗?还是根本就没有离开过?申志强激动得有些眩晕,竟一时不知该做什么、说什么才好,只好用两道绳索般的目光紧紧系住女人,唯恐一错眼珠,女人就会跑掉似的。
看到申志强对自己痴痴呆呆的模样,女人先是一愣,继而眉毛一挑,脸上涌上了一丝怒意。但这怒意只仅仅存在了片刻,便被女人飞快挂上嘴角的一个淡淡的微笑代替了。
“大哥,理发吗?”女人边用一种悦耳的好听的声音问着,边习惯性地一扯头上的帽子,一头秀发果然如申志强所想瀑布般倾泻而下。
申志强心头又是怦然一动:好熟悉的动作!他心里涌起一丝暖意,思绪刚要沿此飞往记忆之乡,突听女人在招呼他:“大哥的头发真的长了,进来理理吧!”女人用扯下的帽子在身上抽打了几下,开开门,把夹在左臂弯的衣服放在门里一张凳子上,然后回头等着他,面上的微笑始终灿烂地盛开着。
女人的笑像一根喜庆的红绳扯着申志强进了屋。
这以后,申志强便成了这里的常客。
再以后,女人成了申志强梦里的常客,他经常在梦中看着倩姨,却喊着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那似乎是一个女孩儿的名字。
“你喊什么,在做梦吗?”妻子常常被他的叫声惊醒,懵懵懂懂中摇晃着他的肩膀问。
他醒来,感觉有泪水从眼角蚂蚁般爬到了耳边。“哦,好吓人的梦……”他掩饰着,翻过身,装作又沉沉睡去。
妻子再次睡去的时候,他却睁大了眼睛。夜色中,倩姨的面孔和另一张脸一会儿在他眼前分开、一会儿在他眼前重叠,仿佛记忆是一扇双拉门,正在被谁狠狠地一推一拉着,折磨得他再无睡意,只好悄悄下床,拉开客厅落地窗的窗帘,心情复杂地凝望着窗外。
又是月中了,圆圆的皓月当空挂着,底色是天空那种寂静的纯纯的蓝。这样晴朗美丽的一个月夜,透过大大的玻璃窗涌进来,便仿佛涌进了一大片瓦蓝瓦蓝的海水,热烈而冷艳,澄明又醇厚,正像此时申志强复杂而摇荡的心旌。
“难道……?”不止一次了,申志强这样一遍又一遍地问着自己,然后又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摇着头,“这,决不可能!”他想,不过是有几分相似罢了,仔细看,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比如倩姨右眉梢上的黑痣,于他的记忆就是极其陌生的……
是啊,他记忆中的那张面孔,是那样的洁白无瑕、晶莹剔透,像东北的冰,似东北的雪,更像今夜这圆皎洁的满月。只可惜,今生,他只能渴求在梦中遇到她了。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思绪至此,申志强不仅悲从中来,他在心里咏叹着这千古名句,不知不觉,泪水悄然打湿了衣衫。
申志强的异常,终于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
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
第四十四章 妻子的怀疑
申志强的妻子叫冷月,在农场机关档案室工作。冷月长得清秀白皙,不仅年轻时是有名的农场“场花”,如今更是别有风韵:细长的眼睛,高挺的鼻梁,虽然嘴巴有些略显微大,但双唇却不失丰满润泽,加之细高挑的个头,高高挽起的发髻,气质上更显压人一等。
冷月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为人正派,生活、工作作风都非常端正、严谨,这给申志强脸上增添了不少光彩,所以结婚几十年来,申志强对妻子是尊敬有加,言听计从。
可随着生活的日渐平淡,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申志强开始觉得妻子身上似乎少了点什么。偏这少了点的什么,恰恰又是他无法说得出口的,那就是女人的温柔和情趣。申志强承认,若以一个正常的标准给妻子打分的话,妻子绝对可以得到九十五分以上,娶妻如此,还不知足么?人无完人嘛!申志强知道自己应该满足,可这心里还是不听话地时时感到遗憾和失落。
申志强的遗憾和失落,冷月一无所知。她认为,只要自己做好一个妻子应该尽到的义务和责任,丈夫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所以她压根就没有想到丈夫会对自己抱有遗憾,更压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深信和深爱的丈夫也会像那些俗男人们一样,会**,并且,再不回头。
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晚上,申志强早早上床睡了觉。冷月在灯下赶一篇工作总结。这样没有交流的夜晚,对他们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了的。
黑暗,在冷月的笔下渐渐浓重起来。夜,很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在嗒嗒地马不停蹄地走着。
突然,床上的申志强突然喊了两声什么,然后梦呓般哭泣起来。哭声呜呜咽咽的,像海风,又像被堵截在闸门横冲直撞的海水,在寂静的夜里充满了无尽的悲愤、忧伤和无助,与他硕大的横卧在床上的身躯显得极不相符。
其实,这些日子,冷月早就发觉申志强经常在梦中喊着一句话,不,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然而每次,她都因为没有听清楚而被他搪塞了过去。所以这次,她并没有惊动丈夫,而是轻手轻脚地走近床边,耐心地等待着情况的再次发生。
这次,一定要听个清楚!她想。
果然,申志强在短暂的停止后,又开始了刚才的呼喊和哭泣。
这次,冷月听清楚了。那确确切切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而且,应该是一个女人的名字,那个名字是——
梅梅!
冷月的心,像有风掠过树梢,突然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她望着还在睡梦中的丈夫,望着沿着丈夫眼角那道沟壑般深深的皱纹一路流到耳际的浑圆泪珠,第一次感觉到了丈夫的陌生,也第一次把丈夫在她心中的印象从“简单粗犷”改写为不可探究的幽井般的“深不可测”。
可冷月认为,再无法探究的幽井她也要试上一试,哪怕井底映出的是她最惧怕和最难以接受的画面。这个对工作充满责任心的女人,在保卫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上也是如此。
第二天下午一下班,冷月专门拐弯去了申敏家,借口说自己过两天准备去地方县城购些东西,问申敏能否同去。申敏这些日子正因为满仓和巧珍的事情心情不好,也想散散心,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冷月就好似满心欢喜地往外走,走到门口时又装作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悄声问送她出来的申敏:“申敏,你哥过去在老家相过亲吗?”
“家里倒是给定过一个,但没成。”申敏回答得很干脆。
“真的定过一个?叫什么名字?”冷月紧追着问,神情颇为紧张。
“大名不知道,只知道小名叫林妮。”
“林妮?”没有得到意向中的答案,冷月有些失落的样子。
“怎么了?”申敏突然觉得嫂子今天有些怪怪的。
“哦,没事。”冷月搪塞地说着,匆忙走了。
冷月回到家时,丈夫申志强还没有回来。冷月走进厨房,扎上围裙,开始淘米、摘菜。
饭做好了,申志强还没有回来。
冷月心中重重地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今天上班,并没有听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或会议啊!冷月便拄着胳膊肘坐在桌边等,像一个满腹心事的思想者。半个钟头后,大院里传来了开门声和脚步声,很快,申志强像从幕后转出来一样,侧进半个身在门口换着鞋。
“怎么这么晚?”冷月站起来,边盛饭,边问。
“哦,开了个会,回来时,又顺便去理了下头。”申志强边笑着解释。
“撒谎!”冷月在心里反驳着,看着申志强放下夹在腋下的公文包,进了卫生间。片刻,随着“哗”的一阵冲厕声,走出来,抓起筷子就吃,不再说话。
申志强生就一副宽厚的手掌,细小的筷子抓在他手中就像两根针。这早已习以为常了的一个细节,如今在冷月看来却是那样的不舒服。
但她并没有吭声,只是把目光探照灯似的朝申志强头上扫去。果然,那里一尘不染、明光可鉴,确实是刚刚打理过的样子。她突然发现最近男人好似特别注重发型似的,而且,过去理头男人都是叫人帮忙在家理,这些日子怎么自己亲自跑理发店了?是做给谁看?还是冲谁去的?平时不擅心计的冷月边不紧不慢地往嘴里扒拉着饭菜,边心思着。突然,她灵光一闪,豁然开窍,故意笑着问:“这理头的手艺看似不错,不知是哪家发屋?”
“哦,是倩姨发屋。”申志强冲口而出,话出口了似乎又觉得回答得太快太明朗,于是又貌似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是一个朋友介绍去的,说那手艺不错。”
申志强的解释让冷月想到两个字:心虚。
冷月不再说话,可她的心里愈发觉得丈夫有问题了。她决定要跟踪丈夫一探到底了。
第四十五章 午夜的伤情
当初冬的飞雪送走了因丰满而笨重得一步三叹的秋天,申志强的生活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从第一次见到倩姨起,他就把冬雪一般厚重的相思交给了这个女人,并用频繁的理发为借口,让相思月光般浪漫地铺满倩姨发屋,也令两个人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每次去理发,看着眼前大镜子里倩姨的一举一止、一颦一笑,申志强都觉着是在沐浴一股春风,温温的、柔柔的、痒痒的,是在冷月身上永远体会不到的令他怎样挣扎最终都不忍离开的那种。更何况,倩姨与他梦中的梅梅是那样的相像,看到她,他就仿佛看到了自己失而复得的青春一样。
而倩姨呢,一直是那样的静如菊、柔若水、轻如风,笑起来是绽放的花,忧郁时是含苞的朵。她的话很少,可每句话透露出的关心却都令申志强心旌摇荡,这更让申志强觉得她就像一本厚厚的书,耐读,可读,愿读。
他就这样如饥似渴地读着,终于有一天不再仅仅满足于“理发”的拜读方式。
那一天,他借着晚上开完班子会往家走的当口,敲开了倩姨发屋那扇已经上了锁的小门,并终于和倩姨双双躺在了倩姨独居生活的那张小床上。
那一次,他更深一步体会到了倩姨的柔情似水,体会到了在妻子冷月身上久已不遇的魅力和激情。
从此,俩人虽然表面上是死水一潭,你赚你的钱,我理我的发,“从容”得很,暗地里却如两株干枯了的老树,在经过了和风细雨的抚慰和滋润后,突然又奇迹般地重新萌发了新绿、充满了生机。
可这种“从容”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
那是一个傍晚,申志强下班回家,没有看到冷月的影子,却发现一张字条压在茶几的玻璃杯下。字条是冷月留下的,上面说,她母亲头痛的老毛病又犯了,她今晚要住在娘家照顾母亲,让他不要等他。
看完便条,申志强心中暗喜:妻子的娘家在另一个农场,虽说不算远,但来回也得一百来里路,怎么说冷月今天也回不来的。他觉得这是老天赐给他和倩姨的又一个绝好机会。因怕冷月往家中打电话找不到人,他决定把幽会地点定在自己家里。当一切过程都在他头脑中设想一遍并确认没有纰漏后,他抓起了挂在墙壁上的电话拨通了“倩姨发屋”。当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句悦耳动听的“喂”后,他只说了一句“今晚九点钟来我家理发”便挂掉了。
因怕有顾客在场猜忌,这是他们约定好了的联系暗语。
九点钟的时候,倩姨像一个幽灵,从后门悄悄潜入了申志强的家。
倩姨刚进申志强家门,便被申志强一把扯进屋里,挂上门,转身抱住倩姨挪至卧室。在看到卧室里那张铺着牡丹图床单的席梦思大床后,申志强突然宛若一头看到了浓重红色的公牛,狠狠地把倩姨摔到床上……
也许是大床的温馨加重了本就被压抑得气喘吁吁的欲火,两人就像两只彻底爆发的猛兽,云雨酣畅数次,直到午夜的月亮荡到了中天才相拥着沉沉睡去。
这一次,他们可以彻夜厮守,不用担心有人会来打扰。
可就是这一次的这一刻,卧室的门突然被悄无声息地推开了,一个人,正站在门边冷冷地看着床上的一切,布满仇恨的脸上挂满了伤心、绝望的泪水。
是冷月!
冷月并没有回到娘家去,她一直躲在隐蔽处等待着跟踪申志强。可没想到没等到申志强出来,却看到倩姨从自家后门儿左观右望地走了进去。
丈夫的**竟然是个理发的!自己在丈夫的心中还不如一个理发的?这让冷月感觉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莫大侮辱。她看着倩姨进屋,没有马上做出反应,而是揣着一颗冰冷的心游魂似地在路灯惨淡的马路上转悠了大半天,估摸着是时候了,便转回来悄悄拧开门锁,把两人抓了个正着。
或许是“做贼心虚”,也或许是夜深人静的缘故,冷月转动门锁的声音虽然不大,却“啪”地一声很清脆,一下惊起了床上蛇一般死缠在一起的两个人。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坐起,然后女的短促地“啊”了一声,慌忙用被子遮住了自己的身体。
看着冷月冷冷的且泪流满面的样子,申志强慌了,他手忙脚乱地抓过一件衣服披上,然后跳下床,语无伦次地向冷月做着解释。
此时,冷月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她无法接受丈夫**的现实,更无法接受,令自己丈夫**的,竟真的是一个在自己面前毫无优越感可言的发廊女子!
申志强的话冷月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她用一种鄙视和怨恨的目光盯视着丈夫,突然觉得过了这么多年了,到现在才发现丈夫就是一只垃圾桶,一只连这种女子都能入眼的垃圾桶!尤其是眼前,他那裹着衣服低声下气的样子让她觉得很恶心。
她想起自己曾经美丽的年华,想起自己这么多年的认真付出,感觉就像一颗石子打了水漂,最后沉在绝望的深水下,再也无法浮起。她的心好痛,同时也滋生起一股绝望的倔强,她毅然擦干泪水,冷笑一声,转身离去。
冬日的午夜街头,寂寞而凄清。几天前刚刚下过的第一场雪,在路灯的映照下泛着清冷冷的白。看过了刚才龌龊的场面,冷月突然喜欢上了这雪路,喜欢走在上面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这声音,此时就像是雪在和她讲的悄悄话,填补了她因绝望已变得空白一片的大脑。
冷月漫无目的地走着,她的脚就像踩着许多往事似的,沉重而酸软,脚下的雪路也随着越来越接近的主街而一段一段地消失了。
没有了雪的悄悄话儿,冷月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不知什么时候被蛀虫掏空了房柱,而这房柱,就宛如支撑了她几十年的自信。如今,自信没有了,她觉得,自己随时都有了倒塌下去的可能。
怎么办?她开始自己问起了自己。
第四十六章 难续的前缘
看事先生走了以后,满仓便陷入了左右为难的沉思。
信吧,自己是个国家干部。不信吧,这一连串突发的怪事也实在让他费解。
他想起小时候弟弟满库有那么-些日子一到半夜就扯着嗓子直腔地嚎,嚎得眼睛都发直,瘆呼啦的。母亲就用一碗小米插上筷子念叨着,满仓就看到碗里的小米真的变少了,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不断地偷那米似的,米快被偷光了的时候,弟弟也安稳地睡着了。
那时,趴在炕沿上看的自己只觉得很好玩和荒唐,不想今天才明白世上有些事情真的不是用常理能解释用科学能解决的。
这样一想,满仓的心就开始倾向于看事先生了。其实,在他的潜意识中,这恰恰也是他的初衷。因为,当一个人已无力去面对和解决一些矛盾和问题时,他只能期盼外来的力量来帮助他摆脱困境,哪怕这外来的力量曾经是他多么不愿意接受或无法理解的。
满仓也是如此。
可如果这样,自己就必须要听从看事先生的话,娶巧珍为妻。
可自己真的能娶巧珍为妻吗?这两天,满仓整夜整夜在黑暗中问着自己。他双手枕在脑下,晶亮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可那该是怎样艰难的一条路啊,岳父岳母那一关有多艰难不说,自己心里的那道坎也许都难以逾越。
是啊,每每想到这儿,满仓的眼前就会浮现出秀秀的模样。而且是那个晚上扒拉着算盘拢账的秀秀、扭转头望着他似嗔似怒的秀秀、躺在他怀里软软的再无声息了的秀秀、化作了骨灰盒上的一张相片了的秀秀……
这时,满仓的眼中就会爬出两条小溪,蚯蚓般缓缓地、无声无息地从眼角滑至两侧耳窝。满仓知道,那个曾属于他和秀秀的最后一个夜晚,就像一颗钉子,已牢牢钉在他的心上了,令他不敢拔、不敢碰,一碰,就是一阵锥心的疼痛。
满仓明白,只有这痛淡去,自己才能够安心娶巧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