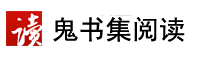第12节
果然,刚一提起满仓和巧珍,铁生就翻了脸,拄着拐杖撑起残腿就要撵赵牌娘出去,并说赵牌娘和当年一样,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铁生的反应早在赵牌娘预料之中,所以她不慌不忙、不急不燥、不羞不恼地对铁生夫妇说:“老铁大哥,当年的事是我鬼迷心窍,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所以今天才想将功补过呀!”
“把个疯子介绍给我们做儿媳妇,这就是你的将功补过呀?你到底又收了谢三娘那个缺德娘们多少钱呀!”铁生的老伴铁嫂本是个性格温和之人,一辈子都没有高声大嗓地说过话,这次听了赵牌娘的来意,也是气不打一处来,边嘴里骂着,边将本来摆在赵牌娘面前的茶水一把端起倒在地上,意在逐客了。
赵牌娘看了眼被溅上晶亮水珠的裤腿儿,讪笑了两下,脸色有些难看地说:“我现在吃的可不再是说媒这碗饭儿了,你们老两口愿不愿意的对我也没什么打紧,所以犯不着这么给我难看,若不是为了你们那可怜的孙子宽宽,我才不会来登你们家门槛讨你们的没趣。”说完站起来转身就朝外走。
一听说为了孙子宽宽,铁生的面色一下缓和了下来。这个视孙为命的老家伙,自从知道了宽宽是自己的孙子后,嘴上不说,心里却没有一天不惦记的。可无奈宽宽是人家巧珍带大的,自己再想,也是一没权力、二没资格。然而此时听了赵牌娘的话,像是黑暗中见到了一道曙光,他来不及站起,便伸手用拐杖挡住了赵牌娘,问:“宽宽怎么了?你有救我孙子的办法?”
赵牌娘本来就不想走的,现在得了面子,便又回转身一屁股坐在木椅上,有些拿腔拿调地说:“我一个老婆子能有什么好办法,不就是想,满仓若和巧珍合为一家后,宽宽名正言顺地就是您的孙子了。这孩子虽说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可我也打听过了,孩子的手脚现在有时可以动些哪,有好转,肯定能好起来!”
“你说的是真的?”铁生夫妇异口同声地问道,睁得溜圆的眼睛中充满了讶异的惊喜。
“我一大早跑你们家来是为了给你们说句谎话么?”赵牌娘慢条斯理地说着,伸手碰了碰面前桌子上的玻璃杯。
杯子空空的,杯口的边缘在透窗而入的阳光下泛着刺眼的光芒。
铁嫂马上不好意思地拿过茶壶,“哗”地一声让冷寂的空杯重新变得丰富而热情。
赵牌娘确实没有说谎话。前些日子,满仓专门花钱从省城请了一位理疗师为宽宽进行恢复治疗。原本也没报太大希望,没成想半个月过去了,孩子的手脚竟有了几次明显的反应,脸色看着也一天比一天红润起来。这一现象让希望宛若阳春的枯草一样在满仓的心中复苏了。谢三娘也暗自窃喜,心想只要宽宽好起来,不愁满仓和巧珍不破镜重圆的。
听赵牌娘讲了上面的事情,铁生老两口更是欢天喜地,铁生不断暗示老伴给赵牌娘往杯里续着茶水,并表示只要能把宽宽弄到他们老两口膝下,一定会给予重谢。
时令已是阳历十一月了,东北人家的屋子里大多都起了炉火。就像此时的铁生家,外屋的小炉膛里炉火着得正旺。火苗像一条条伸伸缩缩的金色舌头,贪婪地舔舐着炉盖,顶得炉盖上的水壶像被迫坐在火炕上的黑矮胖子,头上冒着大汗淋漓的热气,嘴里滋滋滋地喊着救命。
炉上的小水壶咕嘟咕嘟开了三遍的时候,赵牌娘脸上挂着成功第一步的喜悦迈着功臣般的步子心满意足地走了。
赵牌娘走后,铁嫂想着想着突然担起了心,问重新坐回炕沿正眯着眼儿吧嗒着旱烟的铁生:“难道,真的要让咱们的儿子跟个疯子生活一辈子吗?那岂不是苦了咱儿子?”
老伴的话让铁生脸上犹未褪尽的笑容宛如秋雨乍遇初霜,突然凝结起来:是啊,光想着孙子了,却忘了儿子的问题……
铁生神色凝重起来。他沉吟着,半天没有言语,可脸上的风云变幻却显示着他内心正在进行着的极其复杂的斗争。他甚至忘记了夹在指间正在一截一截燃尽的香烟,直到那最后的一点亮色吻到了他的手指并狠狠地咬了他一下,他才梦醒般回到老伴直射过来的等待的目光里。
无毒不丈夫!铁生突然在心里说了句,然后下定决心般狠狠地扔掉手里的烟屁股,对老伴说:“这事你不用操心了,我有办法。”说完,脸上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狠色。
第四十一章 合适的人选
铁生老两口认可的事,在满仓那儿却碰了壁。
那天,就是从铁生家出来的第二天,赵牌娘不顾天上飘起的细蒙蒙的秋雨,坐着公交车便去了牛村。可当她满脸堆笑地向满仓说明自己的来意时,没想到,满仓在说了一句“胡闹腾”后,便看也不再看她一眼地扭头走了。
这让赵牌娘很生气。她也料到了满仓会拒绝,但没想到满仓对她的态度会这样生冷,那神态,就像在驱赶一只上赶子对他摇头晃尾讨好乞怜的小狗。
赵牌娘有些委屈,觉得自己一张炽热的脸贴在了一张冷屁股上,心里嘟嘟囔囔地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父子团聚嘛,你乐不乐意的也犯不着这样一副不把人放眼里的架势啊!
赵牌娘像根被钉在地上的木桩子一样站了半天后,决定去找谢三娘。自从上次受了申敏的冷鼻子冷脸后,赵牌娘便把谢三娘认作了自己的同盟军。
她找到谢三娘时,谢三娘正在屋里灶台上烙着葱花油饼。饼薄薄的,上面嵌着一个又一个绿绿的葱花,下锅前,像一张张白底绿花的圆手帕。下锅后,圆手帕吱吱地响着,很快这一块那一块地鼓起来,仿佛底下有个小老鼠在调皮地东钻西窜似的。很快,饼变得黄焦焦、油滋滋的了,不再是圆手帕,而更像极了圆桌上铺的一张黄黄绿绿的油布。
“油桌布”出锅的时候,辛香的葱花味也随之在屋里屋外弥漫开来,引得赵牌娘不觉快走了几步。
屋里,巧珍八岁的女儿巧巧早已含着手指等在了灶台边。赵牌娘一脚里一脚外的时候,便看到刚出锅的第一张饼被巧巧欢呼雀跃着端进了里屋,喉咙间不觉咕噜一声咽下了一口涎水。
谢三娘还在为上次赵牌娘在申敏面前没有理直气壮地为她说话的事生气,看到她进来,寡着脸。可明白赵牌娘的来意后,马上多云转晴,麻利地把出锅的第二张饼盛在盘子里递给赵牌娘。
两人边烙着、吃着,便嘀嘀咕咕地商量着什么。
下午,秋雨息了,天空在露了几下蓝蓝的脸儿后,又铺天盖地地压来了一阵更寒凉的风。窗外的几棵树,在猛烈地摇了几摇后,粘粘的雪花便开始飘落下来。
冬天,就这样准时地来了。
满仓站在办公室窗前,正沉思着什么时,谢三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带着哭腔说:“满仓,你快去看看巧珍吧,非要抱着宽宽走,说是去找她爹!”她的头上沾满了雪花,这使她的头发看上去又多了几分花白。
满仓来不及多问,转身就往外跑。刚到巧珍家院外,就看到巧珍抱着骨瘦如柴的宽宽站在门口,边哭边往外闯,口里大叫着:“爹呀,你快把我和宽宽带走吧,这个人要害宽宽呀,他用针扎宽宽,他是山娃派来的,他想让宽宽死啊!”旁边,山娃请来的理疗师手足无措地周旋在巧珍左右,左挡右拦着,女儿巧巧也拽着母亲的衣襟哇哇大哭着。
“巧珍!”满仓冲过去,拼命从巧珍怀里夺过软软塌塌的宽宽,随手一把将疯狂扑上来的巧珍推翻在地。
“你,你干什么?”脚跟脚赶来的谢三娘拉起哭得满脸花里胡哨的巧珍,冲着满仓大喊,“你再心疼儿子,也不能这么对待巧珍,这么多年,她替你养着儿子容易吗?现在,她已经人不人鬼不鬼的了,你这么对她,良心让狗叼去了?”
在满仓的记忆里,这是他第一次在谢三娘口中听到的最有劲儿、最着边际儿的话儿。他不觉向巧珍望去。巧珍被他狠狠地推了一把后,正像一只受了惊的兔子般躲在谢三娘的怀中瑟瑟发抖,脸上、头发上沾满了灰土。满仓不觉心生怜惜,走上前去,安慰巧珍说:“不怕,巧珍,有我在,宽宽没事的……”
正当院里乱成一团的时候,有一个人却躲在院外的角落里偷听着、窃笑着。这个人就是赵牌娘。
原来,此时院里上演的一切,正是赵牌娘和谢三娘一手导演的。
下午,理疗师去给宽宽扎针时,谢三娘就按照赵牌娘的嘱托悄悄对巧珍说:“巧珍,昨晚你爸爸托梦给我,说这个人是来害宽宽的,千万不要再让他碰宽宽了。”
巧珍木木地看着谢三娘,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后来,就发生了先前的那一幕。
此时,院墙外的赵牌娘看到事情正按照她的设计顺利进行着,带着一抹得意的笑走了。她要先回场部去,等水到渠成了再来推波助澜一把。
以后的几天,巧珍都处于疯癫状态,尤其见到理疗师,不是抓就是打,弄得理疗师只能站在一旁唉声叹声,却再无办法走近宽宽一步。
“该不会着什么邪了吧?是不是该找个看事儿的给瞧瞧?”一天,谢三娘对满仓说。
满仓本想说“不”,可看看痴傻疯癫的巧珍和躺在床上的宽宽,一时半会儿也实在想不出别的法子来。唉,死马当做活马医吧!他叹口气,点了点头。
两天后,看事儿的先生跟在一走三拧的谢三娘腚后来了。先生先把了把巧珍的脉,又问了生辰八字,然后围着巧珍家的住宅细细观看了半天,最后煞有介事地说,巧珍生来阴气太重,又没了配偶的阳气抑制,导致阴气更甚,总会着些不干净的东西来,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有没有什么破解的法子?”谢三娘和满仓同声问道。
先生掐指沉吟片刻,回答道:“一般的法子是根除不了的,除非找一个阳气重、命里带锐气的男子与之婚配方可。”
“唉,可是巧珍这个样子,哪个男子肯娶哟!”谢三娘急得右手背拍着左手心,望向满仓,一筹莫展。
满仓没有理会谢三娘,他思量半天,问先生:“命里有锐气是什么意思?怎么样叫命里有锐气?”
先生扶了扶鼻梁上圆圆的黑边眼镜,端详了一下满仓,问:“请问这位怎么称呼?”
“我叫铁满仓。”
先生突然面露喜色,镜片后的目光舌头般上下舔舐着满仓说:“刚阳显露,一身正气,名字中又有一‘铁’字,铁乃利锐之器。说句冒昧的实话,您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哪!”
第四十二章 一张旧照片
初冬的第一场雪,让申敏在床上躺了三、四天。但说是偶感风凉还不如说是心里窝囊更加恰当。
从牛村回来后,申敏心里就一直气鼓鼓的,眼前不时出现满仓在巧珍家院里帮雇工一起喂牛的情景。
好你个满仓,秀秀死了还不到三年,你就要移情别恋了,而且还是与秀秀的死有着直接责任关系的巧珍!你对得起秀秀吗?她在心里狠狠地骂着。想到满仓今天的一切,都是哥哥给的,一个念头便新芽破土般陡然冒出:不行就废了他,反正秀秀也不在了!
“铁满仓,你既然不顾及我的感受,也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申敏在心里用一种阴狠得连自己都有些陌生的语气说着。然后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迈开两条鸵鸟般的长腿,气冲冲地向哥哥申志强家走去。
申敏本就生的人高马大,加之新念头带来的力量,病仿佛一下子就好了。
哥哥家是一四合大院,前门后门都通。这天是星期六,申敏从后门进去时,哥哥正好休息在家,并坐在沙发上面向南低头看着什么,听到后面有开门声,忙把手里的东西放到茶几的最低层,然后回头若无其事地对申敏说:“来了!”
“嗯。”申敏答应。
哥哥家外表看着很普通,里面装修得却十分上档次。除了两个卧室、一个客厅外,书房、健身房、卫生间也应有尽有,尤其让申敏喜欢的,是客厅里那两扇自上而下的落地窗,厚厚的,像一堵玻璃砖墙,把阳光无限地引进来,在这初冬的季节,胜过了暖气和炉火。
这样好的住宅,偏偏嫂子还不中意。今年农场新盖了几栋住宅楼,嫂子天天念叨着住楼房哪!
想到这儿,申敏环顾四周,问,“嫂子呢?”
“哦,今天休息,回娘家了。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哥哥边问边一指沙发,招呼申敏坐下。
申敏在哥哥的手势之前就坐在了哥哥对面的那对铺着米色底红印花沙发巾的软皮沙发上,她知道哥哥那是习惯性动作。到哥哥家,她从来用不着客气。
申敏的哥哥申志强,和申敏一样,长得肩阔膀大,坐在沙发里,满满地就像一座小山,以至于他每一动弹,申敏的心都同沙发一起发出痛苦的吱呀声。
“有事?”申志强从茶几下端出一盘瓜子放在茶几上。然后两手交叉在一起,整个上身前倾着,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注视着申敏,仿佛申敏不是他的妹妹,而是他的手下。这是他工作性质造就的习惯,他没办法改变。
“哥,你能不能帮帮我……”申敏是个快言快语的人,话开了头,就炒崩豆般把满仓帮助巧珍的事儿以及谢三娘说的那些气人的话一口气说了出来。
申志强听完,陷入了沉默。他沉默的样子很严峻,厚厚的双唇紧闭着,短而宽的人中上方,一只硕大的鼻子像只威武的坦克在等待命令似的一动不动地趴着。尤其是那两道目光,在隐蔽在厚厚的眼皮下的并不很大的一双眼睛中射出,敏锐得像两道强烈的光柱。
申敏最怕看到哥哥这种神态。因为哥哥的这种神态多数时候是意味着三个字:不可以!
果然,哥哥说话了,语调慢条斯理:“申敏哪,你想过没有,即使我把满仓的职务撸了,不也是更把他推向巧珍那一边了吗?再说,他和巧珍有个儿子,这确是事实啊,你让他一点不挂心那是不可能的,不符合人情嘛!唉,说起来这也都是命啊,是老天安排好了的,谁也改变不了。”说到后面时,他的目光开始变得柔软,脸上充满了无奈。
哥哥过去从来不信命的,现在也……申敏想着,突然发现,几天没见,哥哥好似一下子老了许多,不光是鬓边又增加了白发,就连额上每一根皱纹里,都仿佛挂满了沉重。
这都是因为秀秀,申敏想。过去,秀秀是哥哥生活中的开心果,现在,秀秀变成了哥哥心上的一把刀。申敏不忍心再为难哥哥,她故作轻松地顺着沉默下来的哥哥的目光看到了茶几的最底层。
那里,躺着一张倒扣的已经被岁月腐蚀得有些发黄了的照片。
申敏伸手把照片拿了出来。
那是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满脸稚气,漂亮可爱。
“这是……?”申敏疑惑地问,心里突然跑过了一阵风。
“哦,是过去的一个女战友,这两天收拾东西,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申志强仿佛有些尴尬,伸手拿过照片,摸摸嗦嗦地不知揣在了身上何处。
“可是,她长得好像一个人。”申敏说。
“哪能,这人早已不在了。”
“真的,好像倩姨。‘倩姨发屋’的倩姨。真的,特别像。”申敏强调说。
从哥哥家出来,申敏的心泛起了新的波澜。
照片上的女人就像一个影子在她的眼前晃来晃去。从哥哥的反应中她感觉到,这个女人与哥哥一定有着什么鲜为人知的特殊往事。并且,她还感觉到,这个女人除了长得像倩姨外,似乎更像着另外一个人。而这另外的一个人是谁,她不敢想像她的名字,更不敢说出来,唯恐一说出来,事情便变成了不可逆转的真实。
这如此相像的三个人,究竟有没有什么关联呢?她们的关联与哥哥申志强又有没有关系或有着怎样的关系呢?申敏在街上走着,脚下软绵绵的,像踩了无数的疑惑和问号。不知为什么,自从秀秀死后,她总觉得有一个真相在等待着她,可具体是什么事情的真相她又说不清楚。是秀秀的?还是有关哥哥的?还是别的什么?不知道,总之,她觉得这个真相就像一个彼岸,正在前方一个什么地方冷冷地看着她一步一步地在靠近。
申敏走后,申志强马上松了一口气。他赶紧从身上摸出照片重新锁在床底下一个精致的小木箱里。这只木箱跟了他几十年了,每每家人问起,他都说是一些重要的文件,久而久之家人也就不再好奇和关注。
放好照片,申志强想起申敏说过的话。“像倩姨?”他嘀咕了一句,寻思着:倩姨是谁?
他突然决定要见识见识这个倩姨。
第四十三章 相像的女人
倩姨是“倩姨发屋”的老板。说是老板,其实整个发屋就倩姨一个人。
倩姨不到五十岁的年纪,外来户,除了户籍处,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家里都有什么人,什么背景。只知道大人小孩儿都叫她倩姨,一个人常年住在她那个并不怎么显宽绰的发屋里。
倩姨不善言辞,却不时绽放一朵看一眼便令人难以忘怀的淡淡的笑。那笑,虽然转瞬即逝,但却让人联想到一种静默的美,就像她摆放在墙角的那盆散发着幽香的白菊花。
所以倩姨的发屋虽然简陋,生意却好得很,尤其是那些没职位或有职位的中年男人们,都为了博得这淡淡的一笑而鬼使神差、心甘情愿、走火入魔似的一次次来此做理发、刮脸等消费。
尽管知道这些人的到来多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倩姨在手持剃刀的同时,多余的付出仍然只是一个微笑而已。她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渔者,用最少的鱼饵吸引着更多的来者,使那些愿者上钩的中年男人们,就像一只不谋而合的队伍,成为她的发屋常年的固定收入大军。
申志强很快也加入了这支特殊的队伍。
自从那天听妹妹申敏说了倩姨后,申志强就记住了“倩姨”这两个字,一心琢磨着要找机会见识见识。因为他实在不相信,世上还会有什么人,会与他珍藏的照片上的女人长得如申敏所说——“特别的像”。
那张照片上的女人,是他生命中一个永恒的神话,哪个女人能够打破呢?
所以,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吃过午饭,申志强对妻子说自己出去理理发,便转来转去寻到了“倩姨发屋”门前。
中午,正是人们吃饭和午休的时候,这个时候来,不容易碰见熟人。
申志强来到“倩姨发屋”门前时,一个女人正仰着头从门前横系的一道铁丝上往下收衣服。第一场雪飘过之后,气温一下子降了下来,衣服在铁丝上冻得硬硬的,这就使女人每收一件衣服,都像在掀动一副蝴蝶的翅膀。因为铁丝有些高,女人每取一件衣服,脚跟都要向上垫一下,这时女人就会露出一小截嫩藕般白皙的腰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