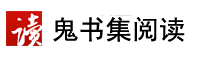第11节
申敏原本人如其身,宽大豁达,通情达理,不好与人争斗,此时想是被怒火冲昏了头脑,一反常态,咄咄逼人,把个满仓吓得步步后退,想解释又插不进话去。
旁边的谢三娘不干了,在她看来,满仓现在已经是她的女婿了,即使现在不是,将来也肯定是。所以她拿出母鸡护小鸡的架势挡在满仓前面,气势汹汹地向申敏嚷道:“是你闺女命短,这怨不得别人。再说了,如果没有你家秀秀,满仓和巧珍当初怎么能分开?”
“什么,你说是我家秀秀拆散了满仓和巧珍?你、你、你可不要血口喷人!”申敏没想到当年做套的谢三娘如今竞倒打一钯,不由气得语无伦次,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话语来顶对。
谢三娘眼里滑过一丝得意的冷笑,看着被她一句话击中“要害”而变得结结巴巴的申敏,她用一种“推倒在地再踏上一脚”的恶毒口气继续说:
“当然!说白了,你家秀秀就是个第三者!”
“第三者”这个词在当年是有一定杀伤力的,不像如今,小三遍地,司空见惯。那时谁家若出了个“第三者“的闺女,全家都会觉得是天大的耻辱,走哪都得挨吐沫星子唾弃。所以申敏听到这儿,气得全身发颤,她厚厚的双唇剧烈地翕动着,却没有发出半点声音,只好突然扭身像院外冲去,脚下噔噔噔地像踩了一阵风。
满仓以为申敏会想不开,冲出去想要劝阻,却见申敏坐上等在外面的出租车,气呼呼地一溜烟跑了。
申敏当然一百个想不开,可想不开就去死,这实在不符合她的性格。她之所以在关键时刻疯狂地离去,不是懦弱地败下阵来,而是要把满仓和秀秀当年的媒人赵牌娘找来,她要让赵牌娘当着谢三娘,不,最好是全村人的面,把当年如何为满仓和秀秀保媒的事一字一句地说清楚,她要为死去的秀秀讨个公道,不能让秀秀白白地搭上性命后,还要在地下毫无来由地受这谢三娘的侮辱和冤屈。
于是,她丝毫没有理会追出来的满仓,坐上车,用几近命令的口气对被眼前情景弄得莫名其妙的司机说:“回场部,开快点!”
出租车唔地一声飞越起来,剩下满仓一人站在门口,愣愣地,好似一时竞忘了自己到底是谁的女婿。
第三十七章 三娘们论理
萝尾村和洼子沟合并后,赵牌娘便搬进了农场场部。原想着场部人多,说媒的生意能更好些,可不曾想这些年刮起了自由恋爱风,“媒婆”行业开始从“热门”变为了“冷业”,媒婆的身份也开始逐渐沦落为人们多多少少嘲讽的对象。
赵牌娘觉得自己的好时候已是车窗外掠过的风景了,只好放下身价,在市场摆起了菜摊儿。
申敏找到赵牌娘时,赵牌娘正在为两毛钱与顾客打嘴仗。正打得欢实时,被突然赶到的申敏老鹰抓小鸡般一把揪住了衣领,扯着就往外走,任凭赵牌娘怎样喊怎样骂也不松手。
到了市场外面,申敏把赵牌娘塞进出租车便奔牛村而去。
农场场部距离牛村不过20多里路,来回半个多点足够了。申敏薅着赵牌娘回到巧珍家时,谢三娘气还没消,正指着蜷在墙角痴痴傻傻的巧珍骂:“你说你除了痴和傻还会个啥?养你这么大,什么都没指望上,临老临老还得接着为你操心......”骂到激愤处,她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正要扯开架势哭号,一转眼看到申敏扯着赵牌娘进了院子,忙一拍屁股又轱辘站了起来,哭天抹泪的样子马上换成了雄赳赳的斗鸡劲头。
申敏扯着赵牌娘径直走到谢三娘跟前,以命令的口气对赵牌娘说:“今天你就当着谢三娘和巧珍的面,说说当年我家秀秀是怎么嫁给满仓的?是秀秀当了第三者,还是你一张巧嘴吧吧地硬给我们往一块儿撮合的?”
赵牌娘被申敏火气撩地一路扯来,本来莫名其妙一头雾水,此时听了申敏的话,心里全明白了。原来就为这事啊!她松了一口气,对谢三娘说:“巧珍她娘,这话是咋说的,什么第三者不第三者的,当年咱不是说好的嘛,”说到这儿,看谢三娘一双眼睛精光闪烁暗示般地直盯着她,吓得马上把已涌到嘴边的下一句话硬噎了回去。她呆呆地直立在申敏和谢三娘之间,眉眼和嘴巴流露着难言的神色,嗫嚅半天,终于看着谢三娘含糊其辞地说出:“我,不说你也明白的。”
谢三娘没想到申敏真的能把赵牌娘找来,自知再揪着以前的事不放只能令自己理亏,就一转话题,说:“我不管以前是怎么回事,我只管以后怎么样?”
“以后怎么样我不管,我只管现在,现在满仓还是我姑爷,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申敏一想起刚才谢三娘护在满仓面前的那个样儿,心里就像不小心吞吃了苍蝇般恶心。
“哎,这你可怨不到我,是你姑爷愿意帮巧珍的,我可没求着他!”说道满仓,谢三娘仿佛又上了发条,来了劲儿。
“这是你说的?那我现在就去叫满仓来,听听他怎么说?”申敏说着就要往外走去找满仓。
“不用找了,我来了。”申敏还没走到院门口,满仓就推开院门走了进来。
早晨,看申敏乘出租车一溜烟地跑了之后,满仓也随后尴尬地走了。为了证明并没有发生了不得的大事,他故意在村里养牛户中转了一圈,故意压下心中的烦恼,与养牛户们谈笑风声着。可他心里终究放不下早晨的事,放不下巧珍和宽宽。这些日子,他每天抽空去巧珍家帮忙,似乎都成了习惯,这冷丁地一放下来,心里竞空落落的。
满仓带着这样的感觉,不知不觉又转回到了巧珍家门前,发现巧珍家院前围了不少人,才知申敏去而复回,两个女人的战斗还在进行。挤上去一听,正听到申敏说要出来找他,便推门走了进去。
看到满仓,申敏像见到了救星,她实在不相信在女婿的心中,女儿还比不上一个疯女人。所以她瞪着一双让期望充灌得有些咄咄逼人的眼睛,说:“满仓你来得正好,你现在就当着大伙儿的面说清楚,是谢三娘缠着你,还是你自己愿意来帮巧珍的?还有,当初秀秀是怎么嫁给你的,是赵牌娘正儿八经儿说的媒,还是秀秀上赶着破坏了你和巧珍的好事?”
申敏一阵连珠炮似的逼问,令满仓满脸无奈和悲愤,他两手插兜,显然在努力克制着心中蠢蠢欲动的情绪,使自己能尽量用一种平和的语气对申敏说:“妈,秀秀已经不在了,你干嘛还这么不让她安生?”没等申敏接话,转身又对谢三娘说,“还有你,当初你对我和巧珍横拦竖挡的,现在也不要想得太多了,我帮助巧珍,是因为我是畜牧站的站长,哪一个养牛户有困难,我都会这样做,不光是对巧珍!”说完,又狠狠地瞪了一眼蔫头耷脑站在一旁的赵牌娘后,气哼哼转身走了。
满仓推开院门时,一群人轰然而散,几只路上觅食的母鸡也吓得扑楞着翅膀跳开去了……
千锤打锣一锤定音。满仓一顿软硬和中的训斥,让三个女人都消停了下来。
谢三娘觉得在众人面前没了面子,冲出院门冲散去的人们喊道:“有什么好看,是不是闲着你们了?”
赵牌娘刚才被满仓那一眼狠盯吓得哆嗦了一下,这会子返过了神儿,想起了自己还摆在市场上的一摊子菜,忙不迭地冲着也气冲冲往外走的申敏喊道:“大妹子,等等我啊!我的菜还在集市上哪!”见申敏上了车,关上车门,丝毫没有等她的意思,便威胁地加上一句:“我的菜若丢了,你得赔呀!”
申敏本身就一肚子的气,觉得女婿今天对谢三娘的态度实在是有些不够坚硬,此时见赵牌娘又来对她大呼小叫,心里说,没收拾你你还不觉闷,觉得没自己的事吗?想到这儿,申敏摇下车窗,狠狠地瞪了赵牌娘一眼,说:“你的菜抵得了秀秀的命吗?”那眼神,恶狠狠的,像两团盯上就能招惹上身的火。
赵牌娘不仅又是一个哆嗦,老鼠见猫般低下头再不敢吱声。
第三十八章 申敏的追忆
一肚子伤心与悲愤的申敏,出了院门便坐上出租车一溜烟儿跑了。
自从知道了赵牌娘和谢三娘当年做套把秀秀介绍给满仓的事情真相后,她就恨极了这两个唯利是图的女人,一心把她们认作了杀害秀秀的凶手。
申敏觉得胸口很闷,突然不想这么早回到那个因为秀秀的离去气氛已变得异常沉重的家,便告诉身边的司机开慢些,她想这样散散心。
出租车就变得不紧不慢地跑着,两旁的风景也从狂奔变成了慢跑,放电影般一幕幕向后退去。
深秋了,路两旁丰收过后的田野就像一只彩鸡,在褪尽了最后一丝斑斓色彩后,呈现出一种喧闹过后的沉静,看去简洁而素雅、开阔而深远、寂寥而苍凉。秋阳映照在曲曲弯弯穿田而过的黑龙江上,也落在白皑连天的芦苇荡中。江风过处,那“半江瑟瑟半江红”的凄美景色直漫至苍茫一色的芦苇荡中,芦苇便金黄黄的像千万只手臂,在水天一色的天地间齐刷刷地挥舞着,并随着出租车的前行而逐渐远去,那千万只挥舞的手臂,便好像在向谁告别似的……
这更加深了申敏的黯然神伤,她坐在车上,想着秀秀的冤死、谢三娘的猖獗以及女婿的背叛,粗犷外表下的一颗女人脆弱的心,令她一反刚才的泼辣与冲动,泪水悄然涌上眼眶。朦胧的泪光中,第一次见到秀秀的情形悄然浮现眼前——
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可在申敏的心中,却恍惚还是昨天的事情。
那时,生活在河南老家的申敏,结婚六、七年了还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偏方用了上百付、汤药喝了快一缸,肚子就是不肯争气地鼓起来。正当盼子心切的两口子正琢磨着去哪儿抱养一个孩子时,远在东北的哥哥申志强回来探家了,并出人意料地抱回了一个女婴。
记得那是一个北风徐徐吹来的季节,孩子五个月大的样子,虽在襁褓之中,却已现出掩不住的眉清目秀和乖巧可人,第一眼便让申敏夫妇爱不释手。
可当时,申志强还没有成家,哪里来的孩子?
迎着妹妹、妹夫疑惑的目光,申志强说,这孩子是他在东北一个村庄的野外捡到的,本应送到孤儿院,可想到妹妹这么多年没有孩子,便千里迢迢抱了回来送给妹妹夫妇抚养。
这个孩子便是秀秀。秀秀长到两岁时,申敏夫妇发现孩子有些跛脚,送去医院检查,说是婴孩时就已形成了,无望医治。两口子心里不免有些遗憾,但转念又想:唉,既然到了咱家,就说明跟咱有天定的缘分,何况,若没有残疾,这孩子可能还落不到咱手里哪!
秀秀越长越大了,也越来越乖巧、漂亮,不光申敏夫妇视为掌上明珠,就连申志强都口口声声说有些后悔把这么好的孩子送给了妹妹。
秀秀五岁的时候,申志强把妹妹一家带到了东北,并把妹妹送到农垦卫校学习了两年,回来后安排在基层做了卫生员。妹夫在老家教过几天书,便也理所当然地当了一名小学教员。
申敏总觉得是女儿秀秀改变了她在老家山沟沟务农的命运,因为她看得出,哥哥对秀秀的喜爱已经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亲生女儿,他之所以把他们一家办到身边,多半是因为离不开了秀秀。
记得有一年,农场闹洪灾,地里的庄稼几近绝产,大米白面成了稀罕物。那年,秀秀八岁,哥哥的一对龙凤胎儿女也已五岁。元旦时,哥哥单位分了三十斤白面,哥哥家也没回,直接背白面去了妹妹家,任凭妹妹妹夫如何退让,哥哥仍是坚持着倒出了多半袋子,并反复嘱咐申敏,秀秀爱吃枣糕,这些白面是专门给秀秀蒸枣糕用的,千万别做了别的用处。说完背着剩下的小半袋回了家,临走还对申敏说:“千万别让你嫂子知道啊!”
这件事一直让申敏百思不得其解。再喜欢还能抵得过自己的亲生儿女?何况还是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也许,是秀秀实在太招人喜爱了吧!”最后,她只能这样定论。
想到这儿,申敏的两眼泪花便化作了满面泪水:这么多年了,除了哥哥,没有人知道秀秀是捡来的孩子,甚至连她自己,有时都怀疑秀秀不是自己亲生的,因为,秀秀已经是她的命了……
可如今,秀秀没了。那么多波浪般调皮的话语,那么多银铃般动听的笑声,都随着秀秀的离去,随着那些真实而美好的日子的远去化作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愈来愈明晰地篆刻在了她的心里,让她无数次怀着柔软的心肠和悲痛的心情在无人的角落或午夜梦回中悄悄地揣摩着、摩挲着,使那一个个曾经真实的片段,就像一面古老的铜镜,在她的念念不忘中越擦越亮,而映出的,却是她越来越憔悴的容颜和越来越显现的老态。
申敏知道,没有了秀秀,她的下半辈子,只能抱着这些回忆过日子了,好在,她守住了一个秘密,那就是秀秀的身世。守住这个秘密,人们就会知道,她曾经生养了一个多么漂亮、多么乖巧的女儿。这会成为她永远的骄傲。这份骄傲,将成为她下半辈子生活的唯一支撑。
可想到这儿,申敏的心又有些不安起来,真的会守住这个秘密吗?
她不由又想起了一个人,一个让她每次见到都有些心慌的人。
这个人叫倩姨,和申敏的家族没有任何瓜葛。可不知为什么,申敏每次见到她,都能在她身上看到秀秀的影子。那动作、那神态、那好听的慢声细语,都好像是从秀秀身上复制过来的一样。
难道,秀秀和她有什么关联?她经常这样一遍遍地问自己,直到问得自己头疼欲裂。
可很快,她又否定了自己的这种怀疑。因为她听说,这个女人年轻时就没了丈夫,也没有再婚,所以根本就没有生过孩子。
这个听说,就像一只熨斗,一次次熨平了她动辄就不安静的心。这个要强又可怜的女人,秀秀的离去,令她就像一个失去珍宝的收藏者,捧着“曾经拥有”的记忆,深陷其中,不想自拔,也不想与任何人分享,哪怕是一丁点儿。
可申敏想不到的是,那个女人,终是她们家族中一个难以绕过的“坎”。当然,这是后话,我们暂且不表。
第三十九章 赵牌娘复出
因为没有坐上申敏带来的出租车,又错过了公交车的时辰,赵牌娘惦记着还摆在市场上的菜摊,情急之下只好动用自己的两条腿往回赶。
二十多里的路程,赵牌娘屁颠屁颠地足足走了一个下午,赶回场部时,已是傍晚五点来钟,市场上的所有摊位都已撤个精光。自己摊位上的筐筐捆捆也全然不见了,只剩下一些烂叶枯皮七零八散地躺在摊位架上或地下。
那可是几千元进的菜呀!尽管早有心理准备,赵牌娘的头还是轰了一下。她四处一看,见还有两个清洁员在打扫被造得一片狼藉的地面,便走上前指着自己的摊位打听货物的去向。
两个保洁员摇了摇头,一脸茫然的样子。
赵牌娘腿一软,顾不上了两个保洁员还在面前,瘫在地上就拍拍打打地哭起来。
赵牌娘正哭到**之处,一双穿着绿色胶鞋的脚出现在她眼前。她仰头一看,一个男人正低头鄙夷地看着她。
男人看上去不到五十岁,肩上搭着一个黄色的旧书包。
“你是谁,想干什么?”赵牌娘边警觉地问,边一骨碌爬起来。
“赵牌娘,想您当年也是一响当当的人物,怎么也会像那些没出息的老娘们似的这么哭啊?脑袋掉了也就碗大的疤瘌,到底什么事啊,至于这样?”男人长的斯文,说出的话却像黑社会。
赵牌娘的眼泪这时已变戏法样猛地收了回去,她扯了挽在肘上的宽大袖子揩了揩颊上东一横西一撇的泪渍,问:“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男人笑了,说:“在这方圆几百里,若说不认识您赵牌娘,岂不叫人笑话?赵牌娘,我是谁不要紧,关键的是我这人特好事,也爱管个闲事儿什么的。怎么样,愿不愿意把你的事说给我听听,兴许我能为你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哪!”
赵牌娘一想也是,反正自己也没有别的人可以去说,不如就说给眼前这人听听,有没有用的发泄发泄也行,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男人听后不以为然地笑了,说:“就这事啊!这事好办,一不做、二不休,您干脆就拿出您当年的看家本事,再为那个满仓和巧珍点上一回鸳鸯谱,第一算是向他们赔了当年的罪,第二又报复了申敏,真正让她少了闺女又没了姑爷,在谢三娘面前丢尽了面子,岂不是更好?”
“好是好,可申敏毕竟是场长的妹妹,我老婆子怕惹不起呀!”赵牌娘心有所动,却又有所顾忌,一副极其为难的样子。
男子哈哈一笑,胜券在握地说:“他官再大,你一个小百姓又能用得着他什么呢?他一个大场长又能把你这一个老婆子怎么样呢?别怕,你若相信我,就先照我说的办,有什么麻烦你就来找我,我会经常出现在这里的。不过,”男子话锋一转,脸色陡然严肃了起来,“这件事,你必须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否则,你我都会有麻烦的。”
看赵牌娘鸡啄米般地拼命点了头,男子似乎才放心地头也不回大踏步走了。
赵牌娘做梦一样站在原地呆了半晌,直到秋凉袭身才开始边寻思边向家走去。待进了家门,主意也拿定了。想着自己今天走得生疼的双脚和一摊子白白丢失的青菜,她咬牙切齿恨恨地说道:
“申敏,当年我能把满仓说成你们家人,现在也一样能把他说成巧珍家人。你欺人太甚,就别怪我不讲往日情分了!”
这一夜,赵牌娘辗转难眠。她在思考着她即将要实施的这个计划的难度。思考着如何才能把一个疯女人说给一个正常男人,尤其是说给一个不仅正常,而且还有着一官半职的男人。她在黑夜中大睁着眼睛,寻找着整个计划实施中的关键切入点,策划着需要进行的每一个环节步骤,以确保自己的马到成功。
赵牌娘就这样想落了星光、想来了黎明,直到鸡叫二遍时,她终于确定了计划的关键步骤,这才带着满意的笑容在正在逐渐明亮起的小屋中沉沉睡去。
许是心里揣着事儿的缘故,太阳还没有完全睁开眼睛,赵牌娘就一个楞儿起了床,梳妆打扮起来,手里一面镜子左照右照的。
几年没有说媒了,赵牌娘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远离了山林的无精打采的飞禽,早已是满身暮气,满腹牢骚,日子也过得白开水一般寡然无味了。可此时这样近距离地端详着镜中的自己,她突然觉得自己仍然风韵不减当年,不由心中又充满了满满的自信,感觉自己仿佛要东山再起了。
赵牌娘不禁感激起昨天遇到的那个男人来,觉得是那个男人的一番话,把已死气沉沉了多年的自己又点燃了起来。
赵牌娘收拾停当,挎上自己已经买了两年却一直不舍得背的一只银灰色包包迈出了家门槛。今天,她要实施自己计划中的第一个步骤,要去拜访一个人。
赵牌娘锁上屋里门,又关好院门,刚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十几步,又想起什么似地转回来。原来,也许是多年没再说媒的缘故,此次复出竟让她神经高度紧张,临上阵了突然觉得有些内急。
赵牌娘摘下肩上的包包挂在院门的木杖上,然后猫着腰一溜儿小跑地奔向了不远处一个茅厕。跑到茅厕跟前,她又停了下来,想了想后又折回院门口,伸手在包里掏出一个本子,胡乱撕下两页后,把本子向包里草草一塞,又连跑加颠地折回了茅厕。
可赵牌娘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本子并没有被塞回到包里,而是由于她的匆忙被搭在了包沿上,并与几秒钟后终于架不住身子的歪斜而悄然坠地。
就在赵牌娘在茅厕尽情放松的时候,一只手,不知从何处伸来,拾起并拿走了那个本子,只余下斜上方的一枚太阳,讪笑着,仿佛在嘲笑着赵牌娘的匆忙与疏忽……
第四十章 成功第一步
赵牌娘要拜访的不是别人,正是满仓的父亲,铁生。
赵牌娘知道,铁生三个儿子,只有小涛一个孙子。可自从秀秀死后,申敏出于对满仓一家的怨恨,便把小涛领回家养着,满仓和铁生夫妇想看一眼都费劲。这完全成了铁生夫妇的一块心病,老两口天天念叨着孙子,梦想着有一天一开门,小涛便会像条可爱的小狗般摇头晃脑地跑进来,可每天,老两口打开门,空荡荡的门口都像一把光溜溜的勺子,在一次次地挖着他们的心。
所以,赵牌娘想,要想说成满仓和巧珍,还得从孙子身上入手,否则,一点门儿都没有。
自从当年和谢三娘一起蒙骗满仓的事情败露之后,赵牌娘就没有再踏进过铁生家。一是自觉羞愧,再者怕铁生夫妇一时激愤做出什么让自己下不了台阶的事情来。可这次,为了自己能出心中的那口怨气,同时也算是弥补当年的过错,这个门槛就是再难迈,自己今天也豁出这张老脸了!这样想着,赵牌娘的底气就有些鼓了起来。能屈能伸才是真英雄嘛!她这样安慰自己。
果然,赵牌娘一推开铁生家的门,铁生夫妇就寡了脸。
“你来做什么?我们家可不欢迎你!”铁生坐在炕沿上,敦敦实实得像一块黑铁疙瘩。
“呵呵…..”赵牌娘讪笑着,磕磕巴巴地说,“是,是,是有人托我来说点事。”说着,自己故作自然地坐在了墙边的一张椅子上。
“说事?那就说吧!”铁生的脸仍是阴呼呼的。老伴铁嫂有些看不过去,倒了一杯茶水放在赵牌娘面前的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