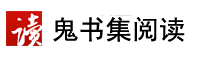第10节
“一个破仓库有什么好谈,就不能说点正事!”铁生没有好声气地说。想到就是为了眼前这个儿子受了委屈的事,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我是想知道这个仓库过去都住过什么人。”满仓从小就看惯了父亲的脸色,受惯了父亲的脾气,所以并不在意,继续追问。
“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不是萝尾村的人!”铁生倔呼呼地说,明显着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再继续下去。
不知为什么,满仓总觉得父亲对萝尾村似乎很敏感,平时说话唠嗑也总是绕着这三个字走,仿佛这三个字就像三只难惹的拦路虎。记得有一次唠嗑时他把牛村说成了萝尾村,父亲便大发脾气,特别纠正说:“是牛村,或畜牧站,但绝对不是‘萝尾村’!”并批评他说话不严谨,不是领导的作风。
这件事当时留给满仓的感觉是父亲太过较真和小题大做,可现在想来,似乎没有那么简单。这让他不得不对父亲的过去产生了怀疑。
也许是因为生气,也许是为了掩饰什么,此时,铁生手里的拐杖与他的那条伤腿一齐上下抖动着。这让满仓心中陡然又漫过了一片新的疑云:自打他记事时起,父亲就拄着拐,并从来不许别人问及此事。问母亲,母亲也是在长长一声叹息后,说:“小孩子别问那么多!”父亲的残腿就在满仓心里形成了一个永久的谜。
难道,父亲的残腿也与萝尾村有什么关联吗?满仓心里快速地想着,嘴上不由脱口而去。“您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不想说?您的腿到底是怎么致残的?您为什么不愿让我知道?”
“小兔崽子,你到底什么意思?来审问你老子吗?”铁生这回彻底爆发了,他呼地撑着拐从炕沿边站了起来,两眼冒火般逼视着满仓。
满仓并没有被吓着,父亲的举动越发加重了他的疑惑,他冒着挨打的危险,在父亲抄起身边的板凳向他扔过来的同时,争分夺秒地再次向父亲甩过去一句话:“我只是想向您了解一些情况,您干吗这么激动?”
“我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你能怎样!”铁生歇斯底里地喊着,气得牛一般喘着粗气。他右手拄拐,左手哆哆嗦嗦地伸向炕沿,想重新坐下。
满仓知道父亲累了,忙上前扶他坐下。他知道,多数这个时候,父亲就像一只使尽了威风的老虎,脾气是不会再发作了。
“爹,您都知道什么,就告诉我吧!”满仓边扶父亲坐好,边小心翼翼地恳求。
铁生没有回答满仓,而是冲门外一嗓子把老伴喊了进来,问儿子回来了准备做什么好饭,然后耷拉着眼皮吧嗒吧嗒吸起了烟,再不接满仓的话茬。
满仓看得出,父亲有意在逃避这个问题,便想到了母亲。午饭后,他刚要问送他出门的母亲,可没等到他发问,母亲便先对他开了口:“满仓,以后别再追着你爹问那些事了,会要你爹命的。”
“为什么?难道我爹以前真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满仓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望向母亲的目光有些游离的忐忑,似乎没有信心接受母亲还未做出的回答。
“唉,不是。想要你爹好,就别再问了。”母亲幽幽地叹了口气后,也像满仓父亲一样闭了口。
父母的表现,让满仓心里像上了一把锁,怎么着也打不开。他没有马上回牛村,而是心情极其复杂地在场部转了一圈,直到想起早上来时听到的冷笑,才急急忙忙启动摩托向牛村赶去,怕回去晚了再碰上什么瘆人的事儿。
阳光开始变成橘黄色的时候,满仓远远地望见了村口。这回,在提心吊胆地经过那些柴草堆时,满仓再没听到“嘿嘿”的冷笑声。
可这回,他却看到了一个人……
第三十四章 自闭的福子
满仓看到的人是福子。福子是巴叔的儿子。
福子患有自闭症,三十几年了没有说过一句话,就为这,如今四十大几了还没说上媳妇。
据说福子十岁之前是说话的,却在十岁那年不知为何突然闭了口,整个人也开始变得孤僻怪异。
满仓听说过福子,可见到本人还是第一次。他之所以认定他就是福子,是因为福子正在做一件事情。
福子正在杀一只漂亮的公鸡!说是杀,其实就是在用手掐!
福子一手反抓着鸡翅,一手拼命去掐鸡的脖子,脸上同时显出极其狰狞的表情。这让满仓很害怕,他看着福子恶狠狠地掐死了鸡,又看着福子用一把铁锹挖坑把鸡埋掉并隆起一个小小的鸡坟,双腿就像被什么钉住一般迈不开了步子。
福子在干这一切时就像没看到满仓一样,直到完成这一切后,才扔下铁锹,抬头送给满仓一个怪异的笑。那笑,在黄昏的夕照下,像一朵带毒的花,又像一道横在他脸上的鞭痕,有几分诡异,又有几分憨直,而更多的,却是怵目惊心。
满仓的目光只与福子的短兵相接了几秒钟,便迅速地避开,而是落在了路边一长溜小小的坟丘上。这里面一定埋着一只又一只的死鸡。他想,心里更加确定了眼前的这个怪异的男人就是巴叔的儿子福子。
原来,满仓刚来牛村不久,就常听村民抱怨说村里养不下鸡,而原因就是巴叔的儿子嗜好杀鸡。他经常把村民家的鸡偷到村外杀掉。福子杀鸡的方式很有限制性,就是必须是用手掐死的,然后也不吃,而是埋起来。村人们也不知他为什么会有这嗜好,又不好跟他这样一个病人计较,想偷偷地去把死鸡扒回来吃肉,可看着福子的样子又觉得不吉利,也就只好作罢,发发牢骚得了。
“那巴叔不管吗?”满仓曾这样问村人。
“管不了哟!”村人七嘴八舌地说,“这个福子很邪性的,听说当年巴叔要搬出这里,可福子说什么都不走,巴叔没办法,也就只好留了下来。”
福子冲满仓的笑只持续了几秒钟,然后就像来了个急刹车,嘎然停止了。再然后,福子就转身倒拖着铁锹走了。
满仓看着福子步履迟缓地消失在夕阳橙黄色的光圈里,心惊肉跳的感觉也开始潮汐般退去。他突然感觉有些累,黎明时的冷笑和对父亲的疑惑还没有在他心头消除,竞又碰上了这自闭的福子的一连串怪举。这牛村,看来真的不是一块安宁之地啊!
唉!满仓长叹了一口气,推起摩托车也不想再骑,便慢条斯理地推着向前走,边走边自嘲地说了一句:“瞧我这站长当的,成了天天捉鬼了……”
“这是怎么了?放着摩托不骑,推着走?”满仓正琢磨着蚂蝗一样钉在他心上的福子的举动和福子的笑,突然,身后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满仓吓了一跳,手里的摩托车差点邪歪在地上。他回头一看,不知何时,老根叔站在了他的背后。这一天一惊一乍的!满仓边想着,边向老根叔打起了招呼:“老根叔,这是干啥去了,这么晚回来?”
“哦,”老根叔抬手指了指背上的竹筐,“上山采点草药,晒干了留着冬天熬水喝,治很多病哪!”老根叔说着,已走到了满仓跟前。果然,背上的竹筐里盛满了各种草药。
“老根叔,您每天都去采草药吗?”满仓又想起了福子的事。
“入秋了,基本上每天都去,想多采点。”老根叔使劲颠了颠身子,使已有些松垮下来的竹筐向上串了串。
“那您每天回来看没看到什么?”
老根叔愣了,他盯着满仓紧张兮兮的脸看了半天,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你是说福子吧!哦,今天没看到,可能是我回来的晚些,但以前看到过。”
满仓回头用手一指,把路边那一小溜鸡坟指给了老根叔。
夕阳下,鸡坟们馒头似地一个紧挨着一个,长长的像一个欲语还休的省略号……
“唉,这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那年,他究竟是看到了什么,还是怎么的?”老根叔的目光在鸡坟上一个个地扫过,思绪,却仿佛飞回到了一个久远的年代,以至于他竞忘记了满仓的存在而喃喃自语着。他的脸上挂满了怜悯,不知是惋惜那个自闭的福子,还是心疼躺在小小坟墓里的受虐而死的鸡们。
“老根叔,您说什么?福子是因为看到了什么才得病的吗?”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被一件件怪事正折磨得晕头转向的满仓听到老根叔的喃喃自语后,像黑暗中见到了一线曙光,他大睁着眼睛望着老根叔,期望着老根叔的回答能成为解开他心中千重疑惑之门的第一把钥匙。可老根叔的回答却出乎意料的平淡无奇。老根叔说:“哦,没什么,我也只是顺口说说而己。”说完,用眼角瞄了满仓一眼,招呼也不打一下,转身走了。
满仓因兴奋已涌上脑海的血液,像遭遇了一股寒流,唰地一下被逼退下来,那种失望,好像马上就要到手的东西突然又被抢走了似的。不知为何,老根叔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他什么,可他总觉得老根叔表现出的一切恰恰正是向他表明了什么,尤其最后的那一瞄,那样的意味深长……
莫非,这个自闭的福子真的有什么故事?当年,他真的是因为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才从此闭口不再说话?他不再说话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守住什么秘密,还是受到了什么惊吓?
满仓呆呆地望着老根叔的背影,苦苦地思索着,像小学生在抠着一道难解的数学题。虽然这道题的解题思路是那样的错综复杂,但跳过解题方式,他已经基本确定了该题的最后答案,那就是——
福子一定是知道当年萝尾村某些秘密的人!
但该如何获得破解这道难题关键环节的解题步骤呢?满仓思来想去,最后把砝码压在了谢三娘的身上。
第三十五章 谁封了他口
满仓把砝码压在谢三娘身上是有一定道理的,虽说当年谢三娘和巴叔并不同在萝尾村,但谢三娘的丈夫李继山和巴叔一直关系甚好,这通过巧珍和山娃的婚事就可足以证明,所以满仓想,巴叔家的什么事谢三娘也应该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从场部回来的第二天,满仓就去找了谢三娘。
满仓一推开巧珍家的院门,就看见谢三娘正往牛圈里抱着伺草。
李继山和巧珍一死一疯后,这个家的一切负担就全部落在了这个女人身上。因为要照顾巧珍、巧巧和躺在床上一直沉睡的宽宽,还要挤奶、交奶、清圈,所以牛就只能圈养了,可这就又为她增加了割牛草、抱牛草这些繁重的活计。
这些没完没了的活计就像山体塌方时纷纷滚落的石头噼里啪啦地向谢三娘身上砸来,令她应接不暇、躲闪不及,只好每天像上了发条的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这样几天下来,谢三娘便心力交瘁,本来就凹陷的眼窝更像塌下去了的一个坑,双颊也变得像被什么吸了进去,整张脸看着就像一张骷髅。
像这个早晨,谢三娘从三点钟就起来忙乎,可一直到现在,脚仍然还没离过地儿,满心的委屈正无处诉说,此时见满仓进来,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亲人似的,扔下怀中的饲草,撩起衣襟就呜呜地哭了起来。
谢三娘的举动,让满仓颇感愧疚。李继山死后,十多天了,他只来过一次。不是不惦记,有几次他走到了门口又转了回去。都说“**门前是非多”,何况他和巧珍之间还有着这样牵扯不清的过去。可现在看来,作为站长,他实在不应该避这样的嫌,让这一家老小的生活无从着落。
他安慰了谢三娘几句,在大院的前前后后、牛圈的左左右右查看了一番后,终于向谢三娘问起了福子的事。
谢三娘满脸的期望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原以为满仓的到来是因为还牵挂着巧珍,不曾想却是另有目的。所以,她像一个渴望关怀的孩子突然落空了满心的欢喜,一下子寡了脸,闭了嘴,倔呼呼地擦干眼泪继续去抱牛草,再不理会满仓一下。
满仓看出了谢三娘的心思,其实这也是他所渴望的。于是,他跟在谢三娘身侧,边帮着忙乎,边说出了憋在心里许久了的话:“巧珍怎么样了?”
满仓的声音并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嗫嚅,可钻进谢三娘的耳中却宛若一声振奋人心的春雷。她放下怀中的牛草,有些激动有些埋怨地说:“满仓,你不能光记得巧珍啊,还有宽宽,他可是你的儿子啊!”谢三娘不愧为心机极重之人,生活都乱成一锅粥了,心思还有条不紊,她知道对于一个成年男人来说,骨肉往往比女人更具有说服力。
满仓的脸红了。他正苦于没有借口进去瞅一眼巧珍,谢三娘的话虽然令他有些难堪,却似一阵及时袭来的风,顺势将他推了进去。
屋里,窗帘还没有拉开,巧珍就在阴暗中毫无表情地坐着,旁边,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宽宽。
“巧珍。”满仓喊她,她毫无反应。
“巧珍,你看谁来了。”谢三娘叫她,她还是不吱声,只管两眼木木地盯着宽宽,脸上呈现着一个始终不变的似笑非笑的表情,直至满仓伸手去拉那道窗帘。
“别动!”她突然喊,声音硬得像突然抛来的一块砖头。
满仓吓了一跳,伸出的手僵硬地停在半空中,目光不解地望向谢三娘。
“就是不让拉窗帘,说什么宽宽在睡觉,拉开窗帘再不睁眼就说明死了。”谢三娘解释着,又嘤嘤地哭起来,“这孩子就是怕真的有一天宽宽没有了,所以宁肯天天是黑夜,这样她就以为宽宽没有危险,只是在睡觉而已……”
“不许哭!”谢三娘话没说完,巧珍突然恼怒地把右手食指放在撅起的嘴唇上,发出了嘘的一声,然后又拍了拍一动不动的宽宽说,“别把宽宽吵醒了,宽宽在睡觉……”
“巧珍,你还记得宽宽?”满仓轻声问,唯恐真的会惊到床上的宽宽似的。
“当然!就是他了!”巧珍似乎有些生气,柳眉倒竖起来,她一指床上的宽宽,说,“他是我和满仓的孩子啊,我怎会不记得!”
“你也还记得满仓?”满仓有些激动,喉头有些发紧。
巧珍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最后沮丧地说,“当然。可是,他不要我了。”说到这儿,突然眼神一变,像变了个人似的站起来去厮打谢三娘,口中哭喊着,“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
撕扯中,一卷纸样的东西从巧珍身上掉了下来。
满仓上前拾起,见是两张已被摩挲得十分陈旧了的百元人民币。他正奇怪着,巧珍冲过来,一把抢走了那两张纸钞,说:“这是满仓送我的,不许你动!”
满仓的眼前霍然出现了十年前他和巧珍告别时的场景。难怪那两张人民币让他感觉如此熟悉、温馨,原来是他十年前送给巧珍的,巧珍竟然一直珍藏着。
这让满仓的心剧烈地痛起来。他原以为,他已经不会再为巧珍痛了,即使有,也已被自己对秀秀的那份愧疚冲淡了,有那么一段日子,他甚至以为巧珍已不在他的心里了。可今天,从跨进这个院子的一霎那起,他才发现,巧珍一直在自己心里还鲜活鲜活的,只是自己一直在逃避而已。尤其眼前,看着那两张纸币,感受着巧珍的痛苦,他的心也像被谁撕扯着一样。
这痛,让满仓发现自己对巧珍的心还是热的。他突然感到肩上突然又多了一份责任。作为一个男人,这个责任,他必须承担。于是,他不顾了谢三娘的存在,勇敢地走上前,握住巧珍的手动情地说:“巧珍,不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会不管你的,你放心。”说完,转身向外走去。
满仓走到门口时,谢三娘喊住了他,吭吭哧哧地对他说:“满仓,福子的事,我知道的并不多。我们虽说跟巴叔的关系还可以,可在这件事上,巴叔还是瞒着了我们,他跟我们说福子是不听话被他打了一顿后变成了这样,可当年我们去看福子时,福子还说了最后一句话。”
“福子说了什么?”满仓紧张地问。
“福子说,‘他不让我说话,我以后就不说了。’当时大家都以为他是说说玩的,可以后就真的不说了。唉!”谢三娘说完,叹了口气,又嘟囔了句,“这事也真够奇怪的……”
谢三娘的话,更加证实了满仓的猜测,一定是福子看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才被人恐吓着闭了口。
那么福子最后一句话中的“他”到底是谁呢?也就是说,到底是谁封了他的口呢?
第三十六章 到底谁女婿
几天后,满仓领着一个三十岁出头的男子进了巧珍家,说是给巧珍家雇的放牛工,并说明工钱由他来出。
满仓的做法仿佛一缕阳光,驱散了积压在谢三娘心头的层层愁云,使她就像一只被晾晒在沙滩上许久了的蛤蟆,在再次沐浴了甘霖细雨后,已近干瘪的身躯马上又气吹般鼓起,且呱呱得意的叫嚣比早前还要得意几分:
“谁说我们巧珍命苦了,虽说死了个山娃,可来了个更好的。说白了,我们巧珍和满仓的缘分那是命中注定了的,任谁也掰不开呀。”她走在村路上,逢人便主动打着招呼,并每次都千方百计地把话题拐到这个问题上来,好让她有机会极尽能事地向人们炫耀她家巧珍的好运和她们家庭即将到来的时来运转。
就这样,满仓和巧珍很快成为牛村人口中又一个新鲜得冒着热气的话题,被神秘而又热烈地传诵着。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再碰到谢三娘这张鼓风机般的嘴巴?于是,满仓帮助谢三娘雇工的事很快就秋风卷落叶般被卷到了满仓的岳母申敏的耳中。
自从秀秀被山娃开枪打死后,申敏就把心中的多半怨恨寄寓在了满仓和巧珍身上,正愁没有出气的机会,这时一听说两人黏糊到了一起,心里的火儿就像憋了许久的山洪突然找到了出泄口一般,哗地就爆发了。她疯狂地推开试图阻拦她的老公,奔到大街上截了辆出租车就赶到了牛村。
申敏在村里转了一大圈,哪儿都没看见满仓,问村人,村人都讪笑着摇头,说:“不知道。”可那讪笑掩盖的背后,却好像有什么寓意在探头探脑,让申敏嗅到了嘲讽的味道。
申敏幡然醒悟,想到这些日子听到的闲言碎语,便让司机把车停在巧珍家附近,自己悄悄地朝巧珍家走了过去。
巧珍家的院门紧闭着,一副很安静的样子。但院内隐隐约约飘出的声音还是暴露了里面的热闹非凡。申敏更加坚定了满仓就在里面的判断,她透过木质的院门缝隙向里看去。这一看,果然恨得申敏差点背过气去。
巧珍家院里,满仓正和雇工一起在牛棚喂着牛,想是这两天多雨的缘故,巧珍家的牛群并没有出村。巧珍家的院子很大,牛棚的右边,是红砖碧瓦的住处,住处正对着院门的厨房敞开着,可以看得见谢三娘扎着围裙在里面颠吧颠吧地忙乎着。灶台上,一只盖得严严实实的铁锅正呼呼地冒着白色的蒸汽,蒸汽中,一股诱人的肉香弥漫了院里院外……
怎么,这日子都这么过上了?目睹了此情此景,申敏这个气呀,她二话没说,不声不响推开院门,冲进院子里劈头就给了满仓一记响亮的耳光。
“谁?干什么!……”满仓正低头干着活,莫名其妙地凭空挨了火辣辣的一巴掌,刚要发火,可抬眼一看是岳母,愣住了,声音也马上低沉了下来,“您,这是干什么?”
“你问我干什么?我还想问你在干什么呢!”由于激愤,申敏的声音完全失了真,就像收音机突然遭遇了电压不足。
“怎么了,怎么了?”谢三娘闻声从屋里跑过来,双手和围裙上还沾着白花花的面粉。她突然看到满仓脸上巴掌大的红印,马上触电般蹦起来,指着申敏大声质问:“你,你,你这个疯婆子,凭什么跑到我家里来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