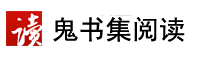第8节
李继山边应答着“这哪,这哪!”边迎着声音走去。到了来人跟前,不由一喜:“是巴叔啊,这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请进,请进。”
来的巴叔是萝尾村的村长。虽然那年月农垦和地方在体制和建设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可李继山和巴叔不仅是老相识,感情上似乎更比一般人亲近得多,这其中的奥妙,当年了解底细的人就不多,现在,恐怕更无从得知了。
寒暄过后,巴叔感觉李继山心情不佳,便毫不顾忌地追问缘由。李继山无奈,只好将巧珍的事托盘而出,并恳求巴叔帮着想想法子。
“堕胎不成,就赶紧嫁了吧。等到显怀就更麻烦了。”巴叔说。
“那嫁给谁呢,谁能娶这样一个媳妇回去!”李继山垂头丧气,往日天不怕地不怕的霸道劲儿荡然无存。
巴叔不再言语。他边往烟袋锅子里装着李继山递过来的旱烟丝,边不动声色地寻思着,沉吟着。烟锅里的烟丝见了底的时候,巴叔从口中抽出烟嘴儿,把烟袋杆儿对着鞋底咣咣就是一阵猛敲,烟灰就一撮一撮地被敲击出来,落在地上,白花花的一层。
巴叔看着一地的烟灰说:“我们村倒有个小伙子,刚从陕西来。从小就没爹没娘,这儿也没什么亲人。小伙子长得不孬,人也厚道实诚,不行给巧珍说说,没意见的话就赶紧把事办了,省得夜长梦多让人看笑话儿。”
“嫁给一个外来的,别人会怎么看巧珍呢?”一边的谢三娘愁眉苦脸地搭了腔儿。
“巧珍她娘,放心吧,小伙子帅得是我村姑娘没一个不惦记的!巧珍嫁给他,面子上也算说得过去。”
巴叔说的小伙子,叫山娃。
巧珍就这样嫁给了山娃。
新婚之夜,巧珍羞涩地问山娃:“我很胖,是吗?”山娃没有回答,只是激动地紧紧拥着她。直到后来,山娃才知道巧珍的那句话,对他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谎言、搪塞和讽刺,而自己的那个拥抱,又是多么的愚蠢、可笑和荒唐。
第二十七章 根叔的疑惑
李继山和谢三娘原以为巧珍未婚先孕的事瞒得天衣无缝,不曾想有一个人却知道得一清二楚。
这个人就是老根叔。
老根叔是萝尾村的老坐地户。可有那么一段时光,他是住在洼子沟的。
老根叔一生娶妻两次,娶第一个妻子时,他在萝尾村,十几年后,妻子病逝,給他留下了一个女儿。第二个妻子,是洼子沟人,除了父母,没有兄弟姐妹。那会儿,正是萝尾村人越走越少的时候,老根叔也无别处可去,便应了对方的要求,领着女儿上门做了人家的养老女婿。可偏偏他跟第二个媳妇的缘分又浅得很,结婚仅仅半年,媳妇便得急病归了天,给他留下了两个需要赡养的老人。
第二个媳妇死后,老根叔很快带着儿子又回到了萝尾村。那时的萝尾村人已走了十之八九,只剩下几户人家因没有去处还留在这里,在村子四处疯长的荒草中,显得格外凄凉。当时,对于老根叔的再回萝尾村,人们只道是媳妇去世后,他既没了理由再住在洼子沟,更没了更好去处的选择,却不知,老根叔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缘于村里的那间破仓库。然而,至于他和这间破仓库究竟有着怎样的神秘瓜葛,这是他自己藏在心里的已很久远的一个秘密,从来不曾向别人讲起过。
在洼子沟的那半年多,老根叔就住在李继山家屋后,有那么一段时日,几乎每个傍晚,他和媳妇都能在自家院里的东墙角上看到满仓。那时满仓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他在李继山家屋后双手拢在嘴边“喂儿哇、喂儿哇”地学着青蛙叫,不一会儿巧珍就穿戴整齐地悄悄溜出来,然后两人心照不宣地一前一后朝村东头走去。
后来,谢三娘带着巧珍去县上医院堕胎,为巧珍做检查的那个女人恰恰又是老根叔的一个叔伯侄女。
老根叔心里是很厌烦李继山的,他每次见到李继山都会在心里骂上一句:“昧良心的东西!”至于李继山如何昧了良心,他又从来不讲。可李继山有一样还是令他佩服的,就是生了巧珍这样俊俏懂事的好丫头。所以老根叔从堂侄女那听说巧珍坠胎的事后,不但嘱咐侄女不要声张,自己多年来也一直守口如瓶。秀秀出殡那天,他在巧珍欲言又止的表情中,就已猜到了山娃犯罪的根由,只是有些纳闷:到底是谁泄露的这个秘密呢?
老根叔年轻时曾在外面闯荡过几年,也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不但不觉得满仓和巧珍做的事儿丢人现眼,还一直为这对离散了的苦命鸳鸯感慨。尤其是眼下。唉!每每想到这里,老根叔都不禁长长叹口气,望着远处发呆。
这天,老根叔正发着呆的时候,一个人走进了院里。
是秀才!
秀秀出事后,老根叔还是第一次见到秀才,本应该寒暄几句的,但因为心情正沉重,便没动。何况,秋阳暖暖的,照得他直发懒。
秀才自己找了块砖头坐下,对老根叔说:“老根叔,看样子,仓库里真的闹鬼哩,不然,这秀秀……”
“你见过?”老根叔用硬撅撅的语气狠狠地回了秀才一句后,杠杠地在脚边的石头上磕起了烟袋。敲了几下后,大概自己也觉得对秀才的态度有些生硬了些,不免接下来又缓和了语气说,“再说,闹鬼也是有因由的,秀秀碍着鬼啥了,鬼怎么能闹她?”
秀才觉得,老根叔话里藏音,似乎很袒护人们口中传说的那个“女鬼”,再者,老根叔今天的心情显然是十分的不好,便不好再说什么。
其实,老根叔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两个问题。一个是秀秀出殡那天,在众多送葬人中间,他看到了一张面孔,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那是一个四、五十岁女人的面孔,虽然岁月的刻刀已在她脸上留下了道道痕迹,可仍掩不住她沧桑下姣好的面容。
那个女人不是牛村人,但似乎也不是秀秀的娘家人,因为整个葬礼,她都独自站在一个角落里,像一朵带泪的梨花。
老根爷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那个女人临走时带走了满仓新居隔壁库房里的一个放了几十年的灰头灰脸的破灯笼。老根爷总觉得,那女人当时看那灯笼的眼神,就像秀才前些时候看仓库桌上的那支笔一样。老根爷的心不禁一个激灵:莫非她和秀才都与这仓库有关?……
这样想着,老根爷便把目光转向秀才,见秀才的身上挂着一个黑乎乎的相机,脑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这念头便是他这几日苦苦琢磨的第二个问题:是谁透露了宽宽的身世?又是谁给宽宽和小涛拍下的照片?
老根叔在心里把知道巧珍未婚先孕的人挨个扒拉了一遍,觉得谁都不可能,便越来越觉得问题出在了自己身上。
他清楚地记得,刚认识秀才时,秀才说自己在写一部乡土小说,需要一些乡土爱情故事,老根叔禁不住他纠缠,便零零碎碎地给他讲了一些本乡本土的事,其中好似有巧珍和满仓的恋爱故事。但当时自己并没有指明是巧珍和满仓啊,而且也隐藏了巧珍未婚先孕的那段啊!怎么就会……?
“老根叔,您别动,我给你照一张。”见老根叔一直沉思地望着远方,沧桑的侧影被阳光镶上一圈金色的光芒,秀才灵感一动,端起了手中的相机,“咔嚓”一声响,把老根叔的思绪拽到了眼前。
难道……?看着秀才手中的相机,他脸色陡然一变,一个念头突然像从深水中倏地钻出的怪物,水淋淋地用一双三角怪眼在他左右两瓣大脑中来回打量着。
这念头让老根叔有些害怕。因为一旦这念头成为真伶伶的事实,他便是杀害秀秀的间接凶手。想到这儿,他的心跳便嘣嘣嘣地变得急促起来。他有些无力地问秀才:
“秀才,宽宽和小涛的照片不会是你照的吧?”
秀才一愣,接着一反常态地跳起来大叫:“老根叔,说什么哪,这玩笑可不是随便能开的!”
见秀才急得抓耳挠腮一副冤屈的样子,老根叔一颗提溜的心又慢慢落回到了肚子里。是啊,哪有那么巧的事?再说了,秀才长得慈眉善目的,除了写书,看样子也做不出别的什么事来。
这样想着,老根叔便拍拍身边的石头,让秀秀重新坐下来。
可是,那个女人又在哪里见过呢?放下了秀才这头,老根叔的思绪又转到了第一个问题上。
第二十八章 勾魂的影子
第二年小粒黄开始收获的时候,山娃被执行了枪决。就像一味儿茶叶,在经过了众多人的不断咀嚼终于失去了最初的新鲜一样,随着刑场的一声枪响,牛村人仿佛终于等到了最后的答案,在长长舒了一口气后,又渐渐恢复了最初的平静。
山娃死后,为了帮助巧珍放养十几头奶牛,李继山和谢三娘从场部来到牛村,在巧珍家居住了下来。
可从场部来到女儿巧珍家之后,谢三娘就感觉自己的身体怪怪的,以往风风火火的她,现在抬下腿就像抬一根木头,头皮也经常有一帮小老鼠跑过似的,嗖嗖地带起一阵风样地发凉、发麻。最可怕的是,最近几天,她竞出现了幻觉。
谢三娘的幻觉很可怕,就是总觉得有一个人站在自己身后,像一个影子。尤其是只有她自己的时候,影子便如约而至,那感觉,就像有水在慢慢地淹过来,然后停住,再然后就一声不响地立在那里,而且无论她走到哪儿,影子都轻飘飘无声无息地跟着,却看不见摸不着。
谢三娘感觉不到影子的脸,只恍恍惚惚地觉得个子应该是高高的。谢三娘很恐惧,她经常干着干着活儿猛地回头望去,或忍不住转过身大喝一声:“谁?”可身后却什么都没有,只有空旷旷的屋子出奇地沉寂。她便长长嘘一口气,抚弄几下心口窝后继续手中的活计。可她刚一低头,感觉告诉她,那个影子又来了……
谢三娘以为影子是山娃的魂魄,想到是自己和丈夫告发了山娃,她心里就胆突突的,认为是山娃回来报仇来了。一天晚饭时,她把这事说给丈夫李继山听,奇怪的是,李继山不但没有表现出惊讶和害怕,还一副低头抬眼的模样望着她,那一双深陷的眼睛在紧紧压低的高高眉骨下突然朝她射出一种恶鬼般阴狠的光,好像怨恨谢三娘突然知道了他的什么秘密似的。
谢三娘从未见过丈夫如此可怕的眼神,她骇然已极,手中的饭碗不由砰地掉落在地上,破裂成两半儿。
谢三娘突然觉得,面前的这个人,仿佛不是她的丈夫。她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又不敢开口询问,只好装作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边低头慢吞吞地去收拾碎碗和撒了一地的米粒,边偷偷窥视着丈夫。
李继山在谢三娘偷窥的目光中很快又恢复了以往的神态,他一边往嘴里扒拉着饭,一边奇怪地看着谢三娘问:“你不好好吃饭低头在弄什么?”
显然,李继山对刚才发生的事情竟茫然不知,这让谢三娘心中的惊恐乌云般迅速聚集起来。“难道,丈夫的眼睛出现了问题?”她想伸手在李继山眼前试探性地晃上一晃,可刚伸手,脑中又倏然闪过李继山刚才莫名其妙的阴冷目光,手便像被烫着一般又急速缩了回来。
从此,谢三娘再不敢过分接近李继山。不知为什么,自从看到了李继山那个阴冷的眼神后,她就总强迫自己把李继山和身后的那个影子联系在一起。“都是高高的个子......”她想着,身上就一阵一阵地发冷。
这样过了一些时日,谢三娘感觉身后的影子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了,她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便决定拿出自己当年天不怕地不怕的泼辣劲儿与影子斗上一斗,好歹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吓人。
一天,谢三娘在接水准备饮牛。水哗哗地流着,很快就接满了一桶。这期间,谢三娘感觉那个影子又来了,正鬼魅般地站在自己身后,盯视着自己。谢三娘关掉水龙头,大着胆子问:“你天天跟着我到底想干什么?有本事你就告诉我你是谁!你是谁!”
谢三娘的声音与以往大相径庭地充满了严厉和威猛,洪钟般在空旷的屋子中回荡着……
谢三娘话音落下,感觉身后有了变化,似乎影子不在了。她松了口气,刚要去拎眼前的水桶,整个人却僵住了,面部也被突如其来的恐惧扭曲得变了形:但见桶中,一张脸正从桶底浮上来,并随着水面的晃动忽而清晰,忽而模糊,忽而浅、忽而深地漂浮着。随即,一个奇怪的影像又透过扁扁的脸从水中映出来。
谢三娘浑身瘫软起来,她本想推翻水桶,却一屁股坐在地上颤栗不已。她惊恐地大睁着眼睛,瞳孔中反射着她刚才看到的一切:一张人脸,毫无表情,却熟悉得像从李继山的脸上刚刚剥离下来。一个牛头,支着两根犄角,在颤巍巍的水中隐隐约约地与脸交叠着,牛眼圆如铃、深如洞,正冷冷地看着她……
谢三娘病了,整日躺在床上动也不动。看望她的人来了三波又走了三波,第四波来的是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婆婆,谢三娘便一骨碌坐起来,吓了老婆婆一大跳。
原来这几日谢三娘并没有病,她之所以装病卧床不起,完全是想避开李继山。今日见老婆婆来了,她就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向老婆婆说了个清楚,寻思着老人们见多识广,也许能给出个什么主意驱驱邪。
老婆婆听了,先是惊惧地睁大眼睛,后又趴在谢三娘的耳根子上嘀嘀咕咕说了些什么。
老婆婆走后,谢三娘便下了地儿,她找了个手电筒揣在身上,然后开始像往常一样里出外进地忙乎起来。傍晚,谢三娘正站在灶台边摘菜,影子的感觉又弥漫了她的全身。待这种感觉已经十分清晰之时,谢三娘突然一个转身,一道刺眼的手电光亮同时急速向后照去。
这一照,谢三娘“啊”地发出了一声瘆人的惨叫。
谢三娘看到了一张脸!
一张毫无表情李继山的脸!
谢三娘的惨叫除了惊走了影子和那张脸,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因为屋里根本就没有可以应声的人。李继山和牛群还没有回来,巧珍在牛圈里做着迎接牛群的工作,宽宽躺在床上还没有恢复意识,整个屋里,除了透窗而入的刚刚升起的冷月之光,其余,全在黑黝黝的暮色中影影绰绰着,并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之中!
谢三娘坐在地上,浑身松软得像一只散了架的破板凳。她想起了老婆婆对她说的那段话:“如果你照见的是谁的脸,就说明天天跟着你的就是谁的魂魄。而这个人的死期也就快要到了,除非有人能够破除……”
难道,真的是丈夫李继山的寿期到了?谢三娘不情愿地问着自己,身子因极度恐惧筛糠一般剧烈地抖动起来。
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屋外村路上传来一阵响过一阵的鞕哨声。是牛群们回来了!谢三娘仿佛从噩梦中突然被惊醒似的,一个翻身爬了起来。“除非有人能够破除……”她想到了老婆婆说的这句话,身上又重新充满了力量,她一个急转身刚要旋出门去找老婆婆,却见一个黑影正向家里跑来。
是巧珍!
巧珍跑到家门口,见到谢三娘,只说了一句话,便又急三火四地旋风般跑远了。
谢三娘再一次瘫软在地,因为巧珍扔下的那句话是——
“妈,快找人救我爹,我爹被牛顶了!”
第二十九章 死亡的约会
自从巧珍嫁给山娃后,李继山对巧珍就一肚子的怨气,怨她自作自受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自己吃苦受累不说,还连累父母承受别人鄙夷的目光而无地自容。加之洼子沟解散后,他自己又从连长一落而成平民,这于他来说无疑是火上加柴,雪上加霜啊!
李继山感到自己的家已经像一棵既老且朽的树,根枯了,干空了,不知还能维系多久?
怎么会到这步田地呢?他经常这样问自己。问来问去觉得根源还在巧珍身上,如果当初她不未婚先孕,如果当初她能嫁个好人家,如果当初……那事情还会是这个样子吗?
李继山这样想着,无处泻火,便经常扬起鞭子,满怀仇恨地啪啪落在那个一半脸黑、一半脸白的绰号“阴阳脸”的奶牛身上,“阴阳脸”的背上便立竿见影地显出几道怵目惊心的渗着细密血珠的鞭痕。
李继山如此狠毒地抽打“阴阳脸”不是没有原因的。一天,他赶着牛群出村的时候,正赶上老根叔去村外采草药,两人顺路走了一段,老根叔就指着“阴阳脸”对他说:“我说你们家这两年会这么倒霉,原来竞养着这样一头奶牛!”
“这还有什么说头吗?”李继山问。
“当然!”老根叔有些嘲讽地对李继山说,“亏你活这么大岁数,这点事都不懂?阴阳阴阳,一半在阴,一半在阳。你家发生的那些事,十有八九都是这头牛妨的嘞!”
从那以后,李继山心里便对那头“阴阳脸”产生了偏见,心里不痛快时就赏它一顿鞭子。
奇怪的是,别的奶牛挨了鞭子,都会或表示抗议或表示疼痛地仰头哞哞两声,唯独“阴阳脸”不,它就像一个倔强的山里汉子,不哼不响地承受着每一次从高空落下的长鞭。这就更加激起了李继山的愤恨,他突然觉得自家的霉运都是这张“阴阳脸”带来的,便更加频繁地挥起了鞭子……
鞭子一次比一次有力,使得“阴阳脸”每承受一次,躯身都要晃动一下,一缕鲜红的血从伤口潸潸流下,滴在黄色的尘土上分外显眼,惊得其他奶牛纷纷哞叫,仿佛在为同伴求情和不平。
“阴阳脸”仍是一声不吭,只是它的眼中开始充血,并开始聚集起阴狠的光。
山娃被枪决的那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李继山做了一个梦。梦中山娃像一个影子,突然出现在并没有开启的门前。他脸色青幽幽的,被子弹打穿的额头还在一股一股地往下流着血。山娃流着泪对李继山说:“老丈人,你害了我,你不但把怀了满仓孩子的巧珍嫁给我,让我戴绿帽子替别人养孩子,还告发我,害我没命,你说,你要怎样还我命来,还我命来!”
李继山吓得魂飞魄散,他仿佛一个跟头从床上摔下来,拼命捣蒜似地向山娃磕头说:“山娃,是我不好,我不是人,可看在我是巧巧姥爷的份上饶了我吧。只要饶了我,让我做什么都成,做什么都成!”
山娃说:“那你明天就去我常放牛的南林子河滩给我烧些纸钱来,你若想活命,就得让我在这边过得好好的,舒舒服服的!”说完,冷冷地扫了一眼狗一样跪伏在地上的李继山,木木地缓缓转过身去,悠悠荡荡地消失在夜幕之中。
天一亮,李继山就匆忙起来。屋里的人都已经起来了。谢三娘在灶间做饭,巧珍已坐在牛肚子下开始挤奶。李继山拿过一个小凳,边坐下和巧珍一起哗哗地挤奶,边对巧珍说了昨夜梦见山娃的事。
巧珍默默地听着,没有一句话,也没有丝毫别样的表情。自从山娃走后,她一直是这个样子,看不出悲伤,也听不到悲声,她本就少言寡语,日子一长,索性便再也不说话了。
挤完奶,李继山吃着早饭,巧珍便出去了,回来时手里多了几卷烧纸递给李继山。
李继山吃过饭,便赶着十几头牛出了村,剩下巧珍在家交奶、清圈。
到了梦中山娃指定的地方,李继山找了块合适的地方,按照风俗习惯面向西南,并在地上画了个缺口朝前的半圆圈,然后把烧纸放在圆圈里点着。
烧纸很快燃烧起来。李继山开始虔诚地念叨祈求山娃原谅他的话儿。
秋日的上午,阳光高高地洒落下来,不燥、不凉。因为远,这是其他养牛户很少愿来的地方,所以四周静悄悄的,除了自家牛群吃草和李继山鬼念经似的声音。
纸打着卷儿燃烧着,一层层像锅底烙熟了的煎饼。没风,可纸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一把把地抓着似的,带着火一张张飞向空中,直飞往西南方向去了。
烧纸全部化成灰烬的时候,李继山突然发现,牛群仿佛一下子没有了咀嚼声,一片参差不齐的阴影,正在早晨的阳光下,从自己身后水一般慢慢袭来。
李继山抬头一看,刚才还在好好吃草的十几头牛,不知何时竞站在了他的四周,把他围在了中间,并一个个大瞪着铜铃般的眼睛仇恨地盯视着他。尤其是那只“阴阳脸”,正抵着锋利的双角一步步向他逼近着,眼里像罩上了一层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