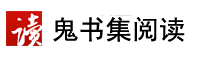第7节
“满仓?”申敏皱着眉想了想,说,“他爹是不是叫铁生,腿残了的那个?”
“对对!”赵牌娘鸡啄米般点着头。
申敏恍然大悟:“你不会是要把秀秀说给满仓吧?”没等赵牌娘回答,她接着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不行,秀秀自己腿脚就不利索,再有个残公公,进了门怎么伺候哇?不行,这我可舍不得!”
“大妹子,这可就是你没有见识了。你想啊,满仓家境是不咋地,可咱可以替他斩断穷根呀!斩断了穷根,伺候公爹,还用得着咱秀秀吗?”赵牌娘对申敏的顾虑似乎早有准备,她并不着急,而是用一种松紧带般张弛有度的语调牵着申敏一步步向前。
“咋斩?”果然,申敏本就大大的眼睛瞪成了一对铜铃铛。
“找你哥呀!”赵牌娘边说边不断地变换着手势,一副指点江山的神态说,“找个机会,给他安排个肥差,或者挂个一官半职,不就得了?满仓这小子脑子好使、做事机灵,从小就有章程,这若有了您们的帮衬还不是如虎添翼吗?还怕将来没有发展吗?”
见申敏还在那目瞪口呆、似信非信、似疑非疑地站着,赵牌娘便问了秀秀的生辰八字,然后从身上摸出一副扑克牌,敲吧敲吧脚边装着布料棉花的包裹,神情严肃地在上面东一张、西一张摆了起来,边摆边暗道:
“这个套,我不信就做不成!“
第二十三章 情伤的旧事 之 成交
赵牌娘摆扑克牌时从来不说话,这就唬得申敏大气不敢出一下,她睁大一双看似并不十分灵活的眼睛,看着赵牌娘那只拇指和食指被烟油熏得黑黄的右手在纸牌间推敲着动来动去,似乎在不断对比、肯定、否定着什么,心里不免充满了疑惑。
这样看着有一支烟的功夫,赵牌娘突然一拍大腿,一声浓厚得蹦自胸腔的“太好了”吓了申敏一跳。
赵牌娘指着摆得棋盘般的扑克牌对申敏说:“从牌相看,这俩孩子的八字合得很,是难得的好姻缘哪!”看申敏还是楞楞怔怔的,她有些生气地砰砰砰地拍着自己的胸脯子保证说,“大妹子,这牌相不会骗人的,我这二十年说媒,就凭的这牌相呀,你去打听打听,哪家的出了差错了?”
赵牌娘说这话的时候,虽然脸上没有丝毫的变化,内心却被内疚和惭愧蛇一样狠狠地咬了一下,因为她突然想起,前几天,她也是用这副扑克牌告诉谢三娘:满仓和巧珍的姻缘合得很哪!
赵牌娘的胸腔里确实装着一颗良心,这良心让她二十年来没有保过一桩亏心媒,今儿个这样,实在是缘于谢三娘那天对她说的那堆掏心窝子的话。想自己在洼子沟这些年,有谁用这样的话暖过自己的心?何况,谢三娘到底是连长的女人,这样低三下四地求自己,自己退一步又何妨呢?
这样想着,良心,便在赵牌娘的胸腔里偃旗息鼓地死去了一般。
赵牌娘的一番话,让申敏的心思也活泛了起来。她早就耳闻了赵牌娘通天通地的传说。通天通地她倒不敢相信,但赵牌娘今天说的每一句话她琢磨着都不无道理。她沉思片刻,突然冒出一句:“那秀秀不乐意咋办?”
“放心吧,依我刚才看哪,秀秀心里早就有满仓这个人了哪!这也难怪,就满仓这样的小伙子,哪个姑娘见了会不喜欢呢!”说着,语锋一转,又拍起了申敏的马屁“当然,咱秀秀更不错,他俩在一起,肯定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人见人羡哪!”说完,不等申敏作出反应,自己就先笑了个花枝乱颤。
赵牌娘的情绪很快感染了申敏。想到自己和赵牌娘相识甚早,相互信赖的关系更是年深日久,觉得女儿的婚事真的是有了希望,不禁也心花怒放起来,非要拉着赵牌娘去附近饭馆吃点饭。
赵牌娘在申敏眼中看到了自己一副功臣的样子,便不再客气,颠吧颠吧地随着申敏去了附近一家饭馆。
饭馆不大,却很干净。因为在商场门口唠过了头,早已不是吃饭的时间,所以小饭馆里很清净。
申敏和赵牌娘都能喝点酒,加之多年未见,今儿个凑在一起,不免举杯你来我去地喝了个酣畅淋漓。开始两人还都清醒,酒过三巡后,便都变得醉眼迷离,舌根发硬。
“老姐姐呀,我说你保媒拉线的这么多年,怎么不给自己保一个呢?你总不能永远一个人过下去吧!”申敏一句话一个酒嗝。
这个话题若在以往任谁都不敢提起,因为赵牌娘怕的不是伤心,是伤“脸”儿。可今天不一样,申敏的出现为她解决了闷在心中偌大的一个难题,她怎么的也得给几分面子不是?
“大妹子,你说什么呢?老姐我不是没有心上人,而是见不到啊!这个没良心的,早死了……”赵牌娘说着,举杯一饮而尽,因为喝得太猛,酒水顺着下巴流进了前胸,像爬进了几条蚯蚓。放下杯时,她的脸上竟似挂上了泪珠。
“别瞎说,老姐姐,老姐夫只是出去打工了,你怎么能咒他死呢?”申敏被赵牌娘的话惊醒了一半。她意识到赵牌娘醉了,便边去夺她手中再次拿起的酒瓶,边劝道,“我知道你心里难受,难受就跟大妹子说说,酒就不要再喝了。”
赵牌娘知道申敏跟她说的并不是一个人。这不能怪申敏,因为除了她自己,没有谁知道她心底的这个秘密。当年她一个人从老家来到东北,就是为了对心中的爱情有一个交代。可几十年的光景过去了,她除了从一个秉性宁静、面容忧郁的女子变成了粗门大嗓、风风火火的妇女外,竞一无所获,连爱情的一点踪迹都没有找寻得到。
这么些年,人们只道她的男人跑了,带走了她的一颗心。却不知,在她嫁给这个男人之前,她的心就已经被一段初恋折磨得脆弱不堪了。而又恰恰是这段初恋,心灯一般,鲜亮着她的人生,温暖着她的岁月,令她每每坐在窗前,孤独地凝视着嫩枝绿叶萌发的颤动时,心里,还能浮升起一丝外人不易觉察的心潮骚动。只是她不想说,怕说出来就破坏了那种凄美的感觉。包括此时面对申敏。这些年,她就这样独自拥有着这种感觉,边享受,边寻找着,寻找着她所谓的对爱情的一个“交代”。
此时,申敏的话,让赵牌娘觉察到了自己的失态。她打着酒嗝,以一个牵强的笑,硬生生拉回了自己有些脱离了轨道的思绪,同时明智地松开了申敏来抢夺的酒瓶。
仿佛又回到了现实中,庸俗势利的习性又慢慢占据了赵牌娘的思维,她突然想到,如果这桩亲事说成了,她将会拿到秀秀、满仓、谢三娘三家的红包,尤其是谢三娘,帮了她这么大的忙,红包一定不会小的了。
想到这,赵牌娘就像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在哭闹之时突然得到了一枚糖果,破涕而笑了。
告别申敏时,赵牌娘感觉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朋友,而是一个商人,一个和她成交了一桩特殊买卖的商人。她有些得意,觉得自己终于对谢三娘能有所交待,又有些落魄,感觉自己明着是打了一个胜仗,其实却败得一塌糊涂。而且这个败仗,不仅令她的道德指数直线下降,还让她的良心和自负从此大大打了折扣。
唉,就当不小心平地摔了一跤吧!赵牌娘这样安慰着自己,却不知,这一跤,竟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第二十四章 情伤的旧事 之 碰壁
转眼,巧珍走了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里,满仓每天都饱受着相思的煎熬。每天,他有事没事都去连部溜达一趟,希望能碰巧接到巧珍的电话,或看到巧珍的来信。可他什么都没有等到,巧珍就像“孤帆远影碧空尽”的一叶方舟,从此竞没有了音讯。这让满仓的心开始了各种惴惴不安的猜测,殊不知,巧珍打给他的电话和写给他的信都被每天坐在办公室的李继山拦截了。
十年前的洼子沟,全连只有一部电话,那就是放在李继山办公桌边的那部公用电话。全连人的所有电话事宜全部由此拨入或拨出。李继山便利用他连长的职权和天生虎超超的劲儿告诉连干部们:无论谁接到了巧珍的电话,都要回复说满仓出门打工赚钱去了,说回来要给巧珍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
八十年代的洼子沟人生活过得不仅不富裕,而且很穷,所以根本就没有心情去管别人的闲事。何况,就凭李继山和谢三娘的为人,他家的事大家碰上都恨不能绕道而行,谁还敢顶风而上?于是,一切便都在李继山的控制和操纵中进行着。
就这样,巧珍每次关于满仓的电话询问,得到的都是一个答案。巧珍不仅相信了,还幸福得流泪了。她就像一只可爱的猫咪,在众人暖洋洋的谎言包围中,眯着眼傻傻地做着幸福的美梦。
转眼,天更凉了。因为一直没有收到巧珍的来信,夜晚,便在满仓的满腹相思中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冷。实在睡不着的时候,满仓便干脆坐起来,面壁抱膝,间或长吁一口气,似乎想挪开不知何时压在心上的那些沉重的东西,可是那些东西像在心里生了根,终是无法移动。
深秋的夜,很静,一切蛙潮虫鸣都不知躲向了哪里,只有一阵阵连夜向南赶路的大雁经过,悲凉地落下些许啾鸣。
这个夜晚,满仓辗转反侧,一夜未眠,赵牌娘夸张的笑声就像一阵夜猫子叫总是在他耳边响起。
昨儿傍晚,赵牌娘百年不遇地来到满仓家,脸上刮着这个家里人平时没有见过的春风,人还没进屋,笑声便报信般先飘了进来。进屋后,屁股还没坐稳板凳,就粗声大嗓地对满仓母亲说“妹子,您家这回可是要时来运转了哪!”没等满仓娘接话,她就麻袋倒豆子般又说又笑地把事情和来意说了个明白。说完了,也不笑了,瞪眼等着这一家大小的反应。铁生夫妇没有吭声,也看不出喜色。满仓则从凳子上忽地站起,没好气地说:“这算哪门子的时来运转,我们不稀罕!”说完气哼哼地向门外冲去。
满仓两只脚刚迈出门槛一只,便被早有准备的赵牌娘抓住了衣襟:“满仓,姨哪,知道你心里有巧珍,可也得人家心里有你才成不是?”
“谁说巧珍心里没我了?”满仓变得脸红脖子粗,一副要打架的架势。
赵牌娘嘴一撇,寡着脸说:“哟,满仓,你赵姨可不是没事瞎嚼舌根的人,人家巧珍早就变心了。不信,问问你自己,巧珍走后给你打过电话写过信没有?”
满仓被噎住了,他想想也是,不觉站在那儿愣怔起来,连赵牌娘走时说了什么都没听清楚。
可不管怎么说,事情不能凭赵牌娘的一句话。满仓就决定天一亮就去找巧珍的父母问个明白。
满仓就这样想着一宿未眠。因自己的小屋没有窗户,他便一遍一遍地起来去看天色。每回起来都弄得那张老床极不情愿地吱吱扭扭叫个不停,前屋母亲就骂“满仓,你干嘛,睡个觉也不消停,尿憋的你呀!”
好容易熬到天亮,满仓爬起来摸起墙角的一只浑身钻满了眼儿的铁桶就往外走。“一大早,死哪儿去?”身后,母亲的声音和着灶烟一起飘来。“下田捞河蟹去!”满仓瓮声瓮气地回一句,头也不回。
说是下田捞河蟹,满仓出了院子就直奔巧珍家去了。
巧珍家的前院里,谢三娘正端着陶瓷缸子满院转悠着刷牙,看见满仓进来,惊愕地张了张满是牙膏沫子的嘴,终还是没有说出什么便转身进了屋。一会儿,李继山边往身上套着衫子边走了出来。“满仓来了?这么早,有事啊?”他问。
“叔,我来问问,巧珍来过电话和信没有?”满仓鼓足了勇气问。
“没有啊。巧珍啊,好像新交了个男朋友,大概挺忙吧!”李继山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像说一件和满仓毫无关系的事情。
“什么?新交了男朋友?”虽然心里早已有了不祥的预感,满仓还是宁愿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是啊!”没等李继山说第二句话,谢三娘便从屋里走出来把话截了过去,她边用毛巾擦着留在嘴边的牙膏沫子,边说,“满仓啊,巧珍她表姐在省城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巧珍很中意,八成是不想回来了。”
如果说李继山的话像一股寒风让满仓感到了阵阵冷意,那么谢三娘的话就是突降的一场暴雪,刹那间将他包裹得严严实实,令他像冻着了似的上下唇哆哆嗦嗦地结巴起来,面部的表情也开始变得僵硬。“啊?真,真的?”他有些不相信地问。
“唉,满仓啊,”李继山接着谢三娘的话头唉声叹气地说,“本来你不过来我们今天也打算去你家把这事说清楚的来。我们也不想这样,可女大不由娘啊,你就别惦记了吧。”
满仓实在不想接受这样的结果,面对着李继山夫妇看似同情实则轻视、傲慢、不屑的表情,他感觉自己既像一个朝贡的败臣,奉上了尊严,却尽扫了颜面,又似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笨鸟,放着广阔天地不飞,非要一大早跑到这里来碰壁!他的脸便先是从红变白,很快又由白转红,一股激愤宛如一头猛兽,在他胸腔里来回冲撞着,难受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愤愤地一个转身跑掉了。
第二十五章 情伤的旧事 之 闪婚
满仓一口气跑到野外河滩边,然后把手里的水桶一扔,坐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思来想去,越来越觉得赵牌娘昨晚的话不像是瞎咧咧,不然为什么这么久了,巧珍连个响动都没有?还有巧珍妈那副得意的神态,真像是巧珍找了个好人家似的,这个女人,向来是狗肚里藏不住二两香油的,八成是真的。
满仓这样分析着,眼里便悄然蒙上了一层雾。想着平日里和巧珍在一起的时候,想着巧珍以往在自己面前乖巧伶俐的模样儿,想着她对自己的温柔和自己对她的好,满仓痛得七零八碎的心里,便又涌起一股暖流,对巧珍怎么也恨不起来。
满仓就在河滩边呆坐着。远处河洼里,是一片苍苍茫茫的芦苇荡。秋天了,芦花开得正旺,白花花像落了一层雪。阵风吹来,芦苇不约而同地随着风势朝一个方向倾斜,好似排练有序的舞者,风来,舞姿绰约,风过,娉婷玉立,并慢慢地在满仓眼中幻化成一个影子——巧珍的影子。他想不起曾经多少个月光如银的晚上,他和巧珍悄悄跑到这里看芦苇,低洼子沟没有好风景,这片芦苇便成了他俩的最爱,也见证了他俩最真挚的爱情。
可如今……
满仓不忍再看,他先是把头埋在自己弓起的两个膝盖间,然后又抬头两眼直勾勾盯着伸向身前的脚尖,直到两脚尖前的土地上爬满了一群又一群急着搬家的蚂蚁,才发现远处黛青色的山岚不知何时漫上了雨雾。雨雾先是一团一团的,后来变成了一片一片的,再后来,就连成了一张大网。大网像渗满了水,沉沉地,从远处一点一点地漫过来,漫到河滩上时,刚才还响晴响晴的天儿,便像一个说哭就哭的演员,淅淅沥沥地飘起雨丝来。
满仓懒懒地站起来,提起水桶无精打采地往连队里走。
雨,无声无息地,越来越密,路上的行人都在抱着头往家跑,唯有满仓孤独地孑行于雨下,感受着凉凉雨丝的无尽受用。满仓感觉到这雨柔柔的,像一把刷子,正在慢慢地冲刷掉他清晨在谢三娘家所受的耻辱,也在慢慢冲刷掉他对巧珍的那份感情和思念。在这冰凉的雨里,他对生活的那份激情和对爱情的那份渴望正逐渐在淡去,甚至消失。他知道,一个旧的满仓正在逐渐死去……
几天后,赵牌娘又满脸堆笑地来到满仓家。还没开口,满仓就抢先问:“巧珍的男朋友是做什么的?”
“哦,”满仓的话问得有些突然,赵牌娘的反应便有些失措,,但赵牌娘只是短暂地愣了一下后马上又回过了味儿来。她故意沉吟了一下说,“好像是在什么公……司,唉,我也说不好,反正听说人长得挺精神,家里条件也不错,在单位好像还是个什么管事的……”
得到了最后的证实,满仓心中最后的一丝希望泡沫般彻底破灭了。他没有向人们暴露他的失望和愤恨,,反倒变得异常平静起来。他知道赵牌娘“猫头鹰进宅,无事不来”,一定是冲着他的婚事来的,所以不等赵牌娘开口,便主动说:“我同意和秀秀的婚事,你和我父母,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说完,若无其事地大踏步走出家门,同时一个口哨,唤走了正蹲在门口伸着舌头打呵呵的大花狗。
看着满仓潇潇洒洒远去的样子,赵牌娘咧着嘴笑了,满仓妈虽苦笑了一下,但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她们哪知道,此时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的满仓,却鼻子酸溜溜的想哭。
“大花,过来,没出息!”见大花狗在拱路边的一只死鸡,满仓一声呵斥,像骂大花狗,又像在骂自己。
“李巧珍,你看着吧,我铁满仓也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他在心里恨恨地说。
深秋的一个早上,满仓不声不响地去农场场部上了班,在农场畜牧科做上了文书工作。赵牌娘怕消息传到巧珍耳朵里,早早地就对满仓妈说,这走后门的事终归不光彩,知道的人越多对满仓不利,所以一定要管住嘴,挺过了这些日子就万事大吉了。
满仓的母亲就按照赵牌娘的嘱咐,闭紧了嘴,谁问就干脆说出去打工了,心想瞒一时是一时吧。
其实满仓妈是打心眼里喜欢巧珍的。这孩子心眼好,又聪明、能干,不像她爸妈那样贼道、势力。可人家毕竟是连长的千金,咱满仓没那好命哟!所以每每去场部见到一瘸一拐的秀秀,满仓妈就悄悄抹眼泪,抹完眼泪还悄悄劝满仓说:“也行啊,人只要图一样就行了。秀秀虽然腿脚不好,可人不丑,家境又好,还给你找了工作,也算是没有亏着咱。”
其实满仓的母亲对秀秀的了解只是凤毛麟角。秀秀虽是在爹妈的宠惯中长大的,却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骄纵、霸道不但没有,柔顺、懂事、善解人意却较一般女孩子更占了上风。这让满仓的心里多少有了些许安慰,加之秀秀的父亲在农场中学教书,母亲在门诊上班,这种知识分子家庭中的那种温馨、祥和的氛围,满仓还是第一次接触到,这让他新鲜,也让他迷恋,更让他向往。在这种环境中,满仓渐渐地淡忘了巧珍,心情,也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在赵牌娘“两人原本就是同学,彼此都了解,犯不上再等”的有目的地催促下,一个月后,满仓和秀秀在农场场部举行了婚礼。满仓妈也不再掖着藏着,虽然满仓是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什么都不用她操心、置办,可这个朴实的女人还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为满仓和秀秀置办了一些她认为还算拿得出手的物件,并专门找了辆手扶拖拉机披红挂彩地送了去。
听洼子沟的老人说,这一天,什么都好,唯独不好的是,后来天边飘过了一道黝黑黝黑的云,直落向现在牛村南岗那个方向去了。
第二十六章 情伤的旧事 之 骗嫁
满仓结婚一个月后,巧珍风尘仆仆地从省城回来了。四个月没有满仓的消息,她的心火急火燎的。所以一进家放下行李,她就急着要去满仓家。她寻思,年根底下了,满仓也该回来了。
巧珍的急不可耐,让李继山和谢三娘的阻拦像两枚被用力掷上铁墙的钉子,在迸发出星星点点的火花后,又急速地退败回来,落在地上,无奈地看着巧珍风一般席卷而去。
巧珍到了满仓家,还没来得急跟满仓的家人打招呼,便一眼看到了对面墙正中端端正正挂着的满仓和秀秀喜气洋洋的结婚照。
“这,是怎么回事?”巧珍脑袋嗡地一声,用一种变腔的声调惊疑地问。
“满仓已经结婚啦,你还来干什么?你不是已经和别人好上了吗?”满仓的父亲铁生没好气地说。
铁生的话像当头一记闷棍,击得巧珍一阵天旋地转,她伸手扶住墙壁支撑了一下,却终因体力不支而瘫软在地。
巧珍被送回自己家里,问明了事情真相后,任凭父母怎么转着圈低三下四地对她说:“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啊!”她仍是不吃不喝、不言不语,并开始一阵阵发烧,憔悴的脸上氤氲着逐渐扩散的红潮。
李继山要去找连队卫生员,被巧珍一声尖叫阻止了脚步。巧珍赌气似地下了床,完全不顾了姑娘家的娇羞,猛地脱掉了套在身上的肥肥大大的衬衫。
“巧珍,你、你的肚子……?”灯光下,巧珍的小腹圆圆地有些微微隆起,像一座小小的坟丘,很刺眼地涌入谢三娘的眼帘。
“我怀孕了,满仓的。”巧珍满腹悲愤,却一脸平静。她眼睛定定地看着桌上的一杯水,仿佛在说着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可这话,却宛若一声惊雷,震得李继山和谢三娘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少顷,谢三娘开始大放悲声。李继山更是一脸的沮丧。再看巧珍,先是两眼直勾勾的,然后突然挥起拳头,咬牙切齿地朝自己腹部打去,打够了,又双手捂住脸,无声地哭泣起来。
谢三娘躲在家里抹了两天的眼泪后,毅然做出了为巧珍堕胎的决定。
为了避开熟人,谢三娘没有带巧珍去农场医院,而是去了地方县医院。
县医院里,一个坐在桌边戴着白口罩的女医生看了巧珍的门诊单子后,很注意地问了一句:“洼子沟的?”
“是,是。”谢三娘连连点头。
女医生领着巧珍进了密室。一会出来,轻描淡写地说:“您闺女**壁膜太薄,不能做流产,做了的话,恐怕今后就再不能生育了。”
“医生,您再想想办法吧,这个孩子我们真的不能要……”谢三娘跟在女医生身后,边随着女医生走来走去,边不断哀求着。
“没用的。“女医生重新坐回到桌子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对谢三娘说,”这种情况任谁都不会给你做的。除非您闺女这辈子不想再做母亲了。”女医生说完,不再理会谢三娘的纠缠,用严肃的语气向着门外等着就诊的人群喊道,“下一位……”
真是天绝人路啊!回到家,谢三娘便急火攻心地病倒了。李继山也像糟了霜打的茄子,整天唉声叹气焦虑不安。过去,两口子走哪都以有巧珍这么个俊俏可人的姑娘为骄傲,如今,看着闺女,却好似突然捧着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拿不得、碰不得、放不得,可怎么办呢?
正愁着,这天,门前的老树上突然飞上两只喜鹊,叽叽喳喳地叫了一阵后,又飞走了。
“家里出了这么倒霉的事,还能有什么喜事?”看着飞走的喜鹊,李继山正没好气地嘀咕着,外面就传来了哒哒哒的四轮子声。李继山伸长脖子望去,见一个人便往院里走,边喊:“李大个子,在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