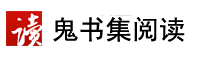第3节
外衣是专门用来干活的,因为怕把臭味带进屋里,每次忙乎完便脱下挂在牛棚的木桩子上。手是要仔仔细细洗上两三遍的,即使这样,举到鼻前,仍有刺鼻的骚臭味道袭来。饭菜在男人的阻止下来不及再去热一遍了,因为来自男人腹内的咕噜咕噜的抗议声似乎比他的吆喝还要响亮。贤惠的女人,这时多半会在灶底的灶灰中扒出一罐烫好的老酒给男人斟上。男人便吱吱地喝着,一副很享受的样子,被风吹了一天的脸颊在灯光下本就红亮可鉴,几口酒下肚后,更是红得浓重,像罩上了一块红布。吃饱喝足后,男人把碗筷一推,懒懒地把自己摊煎饼一样摊在床上。
这时候,应该是九点多钟的光景,是牛村老少爷们儿们一天中最惬意幸福的时候。
这时,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握着电视机遥控器随意地找台换台,可以理直气壮地指使妻子为自己拿这拿那儿,可以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孩子说话斗嘴儿,可以高一声低一句地哼唱自己喜爱的喜剧或小曲。
这时,他们就像一个在长跑比赛中拿了奖牌突然放松下来的孩子,可以在亲人面前肆意地撒娇、耍赖、捣乱,可以提一些稍稍过分的要求,可以做一些稍稍过分的事情,直到疲倦翻江倒海般一波接一波地袭来,直到接二连三的哈欠带出了没完没了的眼泪,才恋恋不舍地在不知不觉中沉沉睡去,嘴角还挂着一丝意犹未尽的遗憾的笑意。也难怪,一天天和牛群泡在河滩草地上,每天只有这会儿,才能够和家人说上一会子话。
随着男人们发出的酣畅的鼾声,牛村家家户外的灯,也相约似地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就像天上的星星,一颗颗地闭上了调皮的眼睛。牛村,就这样在经过了一天紧紧张张、跌跌撞撞、踏踏实实的忙碌后,终于从黎明走到了黄昏,从黄昏走进了夜晚,又从夜晚坠入了梦乡,进入一天中最安静、祥和的状态。
可不知过了多久,就在这安静祥和之下,一声突如其来的炸响却晴天霹雳般划过夜空,引起了牛村一阵惊厥的骚动……
第九章 骚动的夜晚
那是“叭”的一声脆响,尖锐、刺耳,似鞭哨,又像枪声,强烈地撞击着小村的耳鼓,惹得几声狗吠随之而起。
此时,天已完全黑了,在柔柔白白的月光中,停止了一天喧闹的牛村,正俨然一只满载归来的渔船,在晚风温柔和美的拍哄下,一路顺水下流至酣畅淋漓的睡梦中,直到,这一声突然而至的炸响。
“唉,怎么回事?”有女人觉轻,迷迷糊糊地嘀咕。
女人的话还没来得急得到任何响应,夜色中便突然“叭”的又传来一声炸响,惊得女人彻底醒来,欠身坐起。刚刚有些弱下去的狗吠也重新猛烈地狂咬起来,此起彼伏,很快连成一片。不远处,谁家的婴儿被惊厥而啼,洪亮的哭声破窗而出,想是惊扰了母亲,那扇明眸似的小窗内,马上透出了橘黄色的让人感觉暖暖的幸福的灯光。
女人再也无法入睡,披上衣服借着满屋的月光走至窗前。她轻轻地掀开一角窗帘,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响声传来的地方。
窗外,夜已经很深很浓了,正如一副黑色的巨翅包揽着酣睡了的万物。应该是农历十五了吧,月亮银盘似地挂在中天,明明朗朗,洒下一片清凉似水的光晕。可就在这一片溶溶月色编织的宁静中,女人突然感觉,似乎有一个黑影,在远方一处月光无法探及的影影绰绰的屋檐下,“嗖”地灵猿般于她的视野中快速地一闪后,鬼魅般迅速地消失了,再也寻觅不着。
女人心头一惊,像要阻挡什么似的猛地放下窗帘,快速地从窗前转回床边,一只手放在胸口,抚着一颗狂跳不止的心簌簌发抖。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半天,她使劲提了几口气,压下了因紧张惶恐而海浪般一波一波涌上的喘息,声音细弱而惊颤地问着丈夫。她知道丈夫也醒着,因为第二声炸响后,丈夫的鼾声就戛然而止了。
“睡吧,一定是谁家的牛不听话挨了鞭子,有什么奇怪!。”男人似梦似醒地回复了女人一句后,沉沉地翻了个身,中断了的鼾声马上就又接续而起。
女人想了想,觉得丈夫的话也在理儿,养牛以来,自家牛半夜顶架乱群的事也不少见,何况全村这么多家哪!牛村的人虽然爱牛如命,可累了一天了,脾气躁,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像对待不听话的孩子似的少不了甩几鞭子的。至于那个黑影,也许只是自己的幻觉吧!这样想着,女人的心,就渐渐地平复下来,她脱掉刚才慌忙披在身上的外衣,重新上床挨着丈夫躺下。
一切很快又归于了平静。狗儿们因为再没有新的“动静”逐渐放慢、放低了吼声,最后终于停下来,在发出了一声带着情绪似的长长怪声后,赌气般伸长脖子,然后把头侧埋在两个努力向前伸出的前爪中,很快,便和着屋内主人的鼾声咪上了夜色中蓝光闪烁的眼睛。
不远处,孩子的哭闹也开始减弱,最后终于只剩下母亲委婉呢喃的拍哄和轻风一般柔和的催眠曲调。再最后,小窗内橘黄色的灯光也倏然而熄,宛若天边的星星咪上了困倦的眼睛。
外面,不知何时,钩子样的月已下沉了,一片浓云蹑手蹑脚地移过来,黑乎乎的像一只慢爬的怪物,神秘秘的又似一个鬼影。
天气略变了,先是呼啦啦起了一阵风,屋前屋后的树木,便像是有人在用力摇晃起来,摇到不久就落了雨。小村的每家每户,便听到淅淅沥沥的雨声,宛若从远处疾驰而来的千军万马,在迅速地由远而近,仿佛一眨眼,那马蹄阵阵、声声战鼓便已袭至窗前。
这雨,来得及时、来得自然,不大不小、不急不躁,落在铁桶上、打在木桩上、敲在屋檐上、滚在树叶上、润在泥土中,叮叮咚咚、噼噼啪啪、滴滴答答,像众多歌者手中的琴键,此声间歇,彼声响起,彼此呼应,又相互重合,每一下都宛若墙上哒哒的表针清清爽爽地跳跃在人们的心上。这让人们觉得很舒服,横在心上半月有余的粽子样久久不易消化的暑热,也在不知不觉中无声无息地消除殆尽了。
这本是一只再温馨不过了的乡村小夜曲,处处洋溢着和谐动人的音符,可在这个特殊的夜晚,却成为了掩盖罪恶的最得力画面。
这个夜晚,没有人会刻意去留意、辨别、扑捉来自风中的任何异常,也没有人去惊讶、怀疑、猜测刚才的两声炸响,因为——
牛村人实在太累了。一天的辛苦劳碌,让完全放松下来的他们轻若片纸,没有一丝力气,仿佛一股轻风就能把他们扬起来随便抛到哪一个角落里而无声无响。他们也太在乎这每一个安静的夜晚了,对一天中只有此时才能够任意亲近的火炕或木床,他们只想尽情享受,不舍得有任何哪怕是小小的打扰和糟蹋。所以在牛村这个时候的每家每户的土炕或木床上,男人们都和谁比赛似的闭着眼、打着鼾,一声比一声响、一声比一声急、一声比一声有力。在这鼾声中,任何世事都已经十分虚渺,似乎都与之没有任何牵涉。
牛村人的思想也太简单、太朴实了。在他们的心中,小村的一切,都是与牛有关的,除了牛,他们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会和小村扯上关系,除了牛,还有什么能令牛村人作出旁的尤其是恶的举动。
所以,两声炸响,在划过牛村天际的时候,虽然带给了人们些许震惊,但最终还是像一枚石子落入一潭平静的水池,在泛起了一点不大的水纹儿后,迅速地消失了。
小村就这样,梦魇般地轻启明眸后,又沉沉地睡去了,仰在月光下的那张脸依然宁静安详。只是,没有人想到,这两声“叭叭”炸响后,牛村便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从此,再也没有了安宁之日……
第十章 满仓的心事
自从那天晚上听到悚人的哭声以后,站长满仓的心里就像吊着十五只铁桶,每天七上八下的,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尤其是一看到媳妇秀秀,心里就瘆唠唠地发毛。
满仓今年三十出头,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算得上是仪表堂堂。媳妇秀秀年龄和他相仿,有些跛脚,据说是小时候摔的。这就让一些不知内情的人对满仓和秀秀的婚姻产生了疑惑,认为满仓之所以能娶秀秀,不外乎就是因为秀秀的舅舅过去是农场的主要领导之一,现在是农场场长,数万人之上的一把手。
有胆大的人就逗满仓:“行啊你小子,能攀上场长大人的高枝,不简单啊!有脑瓜!”
对这样的话题,满仓除了苦笑,无以回答。因为他之所以能从一个普通农家弟子进入机关科室,又从机关科室一个小小的科员坐到畜牧站站长这个“仕途跳板”的位置,也着着实实是沾了申志强的光儿。
所以,这些人说得也没错。
可即便如此,满仓每天还是感觉空落落的,像是一颗心被谁挖走了一块似的。
其实满仓自己明白,他缺失的那块心,是被一个女子偷去了。那女子不仅偷走了他的心,还化作一个倩影,每天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那是一个美丽的女子,有着天空一般清澈的眼睛和田野一样爽朗的性格。那是他曾经用青涩的青春苦苦追寻的一个梦,直到现在,这梦还在他心里孤独地灿烂着,像一盏灯,温暖着他的生命和日子。
这也是满仓之所以自荐来牛村任职的原因。因为那女子就生活在牛村这片天空下。像月老搭错了红线,女子嫁给了外地来的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虽也英俊结实,却总是脱不去庄户人的土腥、山里人的敦憨,闷实得像块石头。
嫁给了外地来的年轻人的女子,就像温室里的花朵被移栽到了草地上,经过了阳光的暴晒、风雨的敲打后,扑棱棱地长出了许多野性。来到牛村后,满仓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她扎着花围裙,洗衣、做饭、拴牛、挤奶,一身灰满脸汗屋里屋外地忙乎。每每这时,他的心就像误入了刺玫园,躲也躲不开地一阵阵刺痛,觉得那细细的腰身、嫩藕似的手臂,实在不应该与村里这些脏活、苯活、累活扯上关系。
越是这样想着,满仓就越忍不住要有意无意地找机会接近那倩影。可接近了又能说些什么呢?
有一次,两人在村路上偶然走了个对头,竞都尴尬得好似无地自容似的。最后还是对方一低头从他身侧急速而过。那神态,既像一朵含羞颌首的荷花,又似一支忧郁静默的丁香。
那是他到牛村后与她的第一次单独相见。他曾为这第一次相见储藏了太多太多的话语,可没成想最终还是彼此缄默着擦肩而过了,只留下那些话语,堵在他的喉咙,像一群失落的孩子,赌气着不肯回去。
这让满仓很难受,当时他站在原地,没有回头,却清晰地感觉到她在他身后的村路上越走越远。他很想回头喊她一声,像十年前他们在一起时的那样。可他张了张嘴,却不知为什么没有发出声音。
就在那时,他突然发现,那个十年来在他心里翻来覆去呼唤了几千遍几万遍几亿遍的名字,此时涌到嘴边却突然变得那么陌生,就像一颗他珍藏了许久的宝贝,有一天他再次捧出欣赏时,却突然叫不出了它的名字一样。
十年前,他和她曾有过那么一段美好热烈的恋情,可十年后的今天,面对面,他们却恍如隔世,形同路人,满仓的心中不禁涌起一团浓重得任他怎样都无法化开的悲哀。
满仓就在这悲哀里前行着,努力充当着他必须充当的每一个角色,直到有一天他发觉了秀秀的可贵。
满仓的媳妇秀秀虽说腿脚上有些毛病,却生得白净、长得能干。更关键的是,有素养、知大局、善解人意。这个从不多言多语的女人,早在丈夫任职牛村前,就闻知丈夫和这里的一个女子好过。她并非没有揣摩出丈夫来牛村的用意,只是坚持着不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因为,聪明的她知道,太过强烈的光,只会让丈夫觉得刺眼而更加极力躲闪。
于是,她在加倍体贴关心丈夫的同时,也努力琢磨着怎样才能让丈夫更加欣赏自己。
正巧,这年,村里分来了两个大学生、一个卫生员。三个单身汉,吃饭成了**裸的现实问题。秀秀就在这上面动了心思,自作主张地在家里开起了小食堂。
别看秀秀腿脚不好,干起家务却马溜利索,饭菜做得香,人也热情好客,所以不仅拢得村里的这三个人“打都不走”,就是上面下来检个查、兄弟单位参个观什么的,也都愿意上她这儿来落个脚儿、说会话儿。每月下来,不仅能实实在在的赚几个零花钱不说,还增加了满仓与上级领导的沟通机会。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了满仓有个能干又聪明的媳妇,对满仓和秀秀婚姻的偏见也改变了许多,说:“难怪满仓能娶秀秀,虽说跛脚,却是个贤内助哪!”
秀秀的做法,不仅让满仓对她刮目相看,就连满仓的家人们也越来越认定秀秀就是自家的“福星”,不免时不时对满仓敲起了警钟。
一次,满仓和弟弟喝酒,弟弟借着酒劲儿教训他说:“哥,你对不起嫂子。嫂子多好啊,除了腿脚有点毛病,哪儿你能挑出毛病?你想想,没有嫂子,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还不得天天两脚泥一脸土地在地里刨食?哥,嫂子可是咱家的大恩人哪!你可不要老活在过去那点事里了……”
弟弟的酒后一番“真言”,像蘸了水的鞭子抽痛了满仓。他思前想后、抚今追昔,也觉得自己确实对不住秀秀,便暗下决心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纷乱的感情,重打鼓、另开张,一定要真正的对秀秀好起来。
他想,最近的各种骇人感觉,大概是老天在埋怨他对秀秀的不屑和冷淡吧?便寻思着找个机会向秀秀好好表白一番。
第十一章 突发的惨案
有了这个想法,满仓就每天留心寻找着机会。
这天傍晚,月亮在轻纱般的薄雾中穿行着,忽明忽暗。草丛中繁密的虫声、如潮的蛙鸣,交替混杂着落雨般洒落窗前。时令已是农历七月,微风摇荡的大气中,草香、果香和稻香融在一起,就像不大不小的顽皮孩子,在每家每户夜晚关窗的那一刻,雾一般地漫进屋内,浓浓的,久久不肯散去。
这样的空气,让满仓感到兴奋和舒畅。吃过晚饭,收拾完碗筷,看秀秀拿出厚厚的一摞票据准备拢账的样子,刚刚喝了点酒的他也拉了张凳子挨过来,准备借此机会好好与媳妇套套近乎。
秀秀并没有理会他,只是噼里啪啦地拨打着算盘,神情专注得像一个在认真考试答题的小学生。满仓讪讪地等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把头凑过去,近乎讨好地问:“老婆,这个月怎么样,还可以吧?”
秀秀没有马上回答她,而是在完成账目的一个小结后,奇怪地扭过头看着他,明亮的日光灯下,俊俏的脸上写满了调皮的讶异。在她的记忆中,结婚这么多年,丈夫还是头一回对自己表现得这么殷勤。这种感觉真好!她既意外又激动,心里喜滋滋地涌上一股暖意。
满仓被秀秀看得有些不好意思,神情开始不自然起来,被酒精拿得有些微红的鼻尖,此时也变得更红了,像一只红透了的薄皮辣椒,映在擦得油明铮亮的饭桌上,在明亮的日光灯下,一点红变成了一片红。
“去去去!酒气哄哄的。”为了掩饰心底的喜悦和紧张,秀秀把满仓的头推转了九十度,撅着嘴儿撒娇地说,“挣多少都跟你没关系,谁让你当初不支持我来着,所以呀,这是我自己的辛苦钱,年底我要用这些钱买几套好衣裳哪!”
“当然,应该买,随便买,钱不够的话我来赞助!”满仓还是第一次看到媳妇半嗔半怒的样子,不禁心里怦然一动,觉得媳妇原来也是这般的漂亮和惹人怜爱。
这与他以往的感觉大大相反。以往,他看到秀秀一步一跛的样子心里就犯堵,所以平时尽量找借口不让秀秀出门,怕秀秀前脚走,后脚就给他引来一串关于他俩婚姻如何如何的纷纷议论。可此时,他开始感激起秀秀的坡脚了,若不是这样,这么个贤惠漂亮的人儿哪会嫁给他这个原本一清二白的穷小子?他满仓又哪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想到这儿,满仓心里不仅对秀秀更加深了愧疚,还平添了惋惜,觉得和秀秀结婚后,那么多本该幸福美好的日子,都因为他对秀秀的冷淡而白白虚度了。
那么,就从这一刻开始弥补吧!他下决心似地长叹了口气,伸手欲去拥抱秀秀。可就在此时,不知为什么,屋顶的电灯突然倏地灭了,屋里的一切,顿时被一片浓浓的黑暗所吞噬,半天,才在窗外透进的月光中隐约露出些许面容。
“怎么偏偏这当口停电了?真扫兴!”满仓一边埋怨地嘟囔着,一边趟着满地如水的月光小心地移步到墙边的柜子旁,弯腰在柜子的抽屉里悉悉索索地摸出一截蜡烛点上,又倒低烛头滴了些蜡油在桌角上,然后不慌不忙地把蜡烛稳稳当当地坐在蜡油上。
蜡烛的灯捻哔剥爆响着,摇曳的烛光立刻把黄黄的光晕铺满了屋子。
烛花一跳一跳的朦胧中,满仓情难自禁,感觉心中像有花一样的东西要盛开,撩拨得他再次拉起秀秀的手,意欲继续刚才的“表白”。
可表白刚要开始,又一个意外状况出现了:但听窗台处哗啦一声,随后跟着“叭”的一声炸响,接着,一股风仿佛从窗外骤然吹进。
烛焰好像一个身姿曼妙的舞女,在使劲地摇了几摇纤细的腰身后,终于不甘地熄灭了。黑暗中,满仓在感到凉风嗖嗖的同时,也似乎听到了风中夹带着的秀秀没有说完的半句甜腻腻撒娇的话“讨厌,灌点猫尿就……”
“怎么回事,是暖壶炸了吧?”满仓想到整日放到窗台上的暖壶,问。
没有人回答。四周突然变得死一般沉寂。
满仓怔了一下,伸手去摸桌上的蜡烛,却突然感觉到,不知何时斜倚在了自己身上的秀秀随着他的起身在软塌塌地向下滑去。
满仓一惊,酒顿时完全醒了。“秀秀!”他大喊着,左手搂住秀秀的腰,右手拼命去扶秀秀不由自主向后仰去的肩头,试图以此托起秀秀的头。可惨白的月光下,满仓猛然发现,秀秀象牙般莹白的颈项处像是星星点点地溅满了什么?
在短暂的呆愣过后,满仓突然想起刚才的那声炸响,心,不由得一阵恐怖地狂跳。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战战兢兢地伸手向秀秀的脖子上摸去……
触摸处,湿漉漉、黏糊糊、热乎乎的,像……血?!
啊?!满仓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他大张着因惊骇而忘记了闭合的双唇,半天,才本能地抬眼向月光**裸射进的地方望去——
窗玻璃上,一个好似被什么击开的洞,在夜色深浓的背景中,在月亮突然变得极其诡秘、极其挑剔的眼神的暗示下,正宛如一只形状极不规则的怪物的眼睛,在阴森森地盯视着他……
满仓猛地打了个冷颤。他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抱起已滑落在地的秀秀软塌塌的身体,像被泼了一身冷水似地浑身颤抖着,厚厚的嘴唇在剧烈地翕动了半天后,终于像被什么东西撞击喉管般发出了一声难听的似哭非哭、似吼非吼的野兽般的悲号——
“老婆啊!”
悲怆的呼号,没有改变罪恶的发生,却引得黑压压的一堆云急速聚拢过来,逼得月亮的光影在云层后若隐若现地游离着,最后终于超过了黑云的脚步,挣脱了云层的束缚,挣扎着露出了半张脸,却终是带了一种残缺的凄美。
第十二章 秀秀的葬礼
在牛村,每一个夜晚,疲惫,都像一张厚厚的棉被,死沉死沉地压在人们身上,让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尽情地享受着深睡的幸福。
昨夜的两声炸响没有唤醒小村的人。炸响后不邀而至的细雨,更鼓点般催深了他们的睡眠。直到清晨早起一个惊人的噩耗迅风一般地传来,人们才像凭空挨了一记闷棍,个个眼睛都立楞了起来,嘴大张着,惊愕地说不出话来。
秀秀昨夜被人开枪打死了!
秀秀是被连夜送往农场医院的。尽管救护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跑着,可到了医院,秀秀还是在满仓悲怆的呼叫中停止了各项生命体征。
牛村出现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也呈现了成立以来最肃穆的气氛。
这个早晨,牛村的所有出口都被戒严,只许人进不许人出。
牛群是无法赶出的了,这一天,人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等待和接受着几个警察正在进行着的挨家挨户的走访调查。
秀秀的尸体在场部医院就被抬走了,说要经过法医鉴定。村里就有人说:“还鉴定个啥,凶手都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了。”
凶手是已经连夜潜逃了的村里的山娃。
这个长着大耳朵、圆脑袋的村人眼中最老实、最憨厚、最本分的年轻人,不知为什么昨晚在开枪打死秀秀后,又疯了般持枪向原萝尾村村长巴叔家奔去,结果没有打死巴叔,却被巴叔家人认了个真亮儿。
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满仓的弟弟满库从场部回来了,带了几个人在满仓家门前一声不响地搭起了棚子。人们立刻明白了咋回事,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儿赶来帮着忙乎。
“满库,这秀秀,还要回来么?”人们边帮着忙乎边小心翼翼地看着满库的脸色问。原来,当地有个习俗,就是横死的人不能从家里出殡,说是对家人不好。
“唉,本来是不应该回来的,可我哥不干,死活非要我嫂子再回来看看家。”满库眼睛肿肿的,两只眼球上布着一丝一缕的红血丝,像傍晚西天上的火烧云。
小秋的太阳比三伏的还要毒辣几分。秀秀的尸体不能久放,只好第二天便出殡了。
次日早晨,人群、花圈、哭声,悲哀的气氛笼罩了整个牛村。牛村,像一株突然被风干了水分的白杨,每片叶子都默哀般蔫蔫地下垂着。
所有的人都在忙碌,只有满仓,没有泪、没有话、也没有动。他坐在秀秀的灵柩前,瞪着散乱无光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被尸布蒙盖的秀秀。自从那晚那声悲天怆地的呼号后,他便噤了声,停了思想,只余下一副空空的皮囊,木然地面对着眼前的一切。他眼皮肿胀胀的,却仍盖不住红得可怕的眼珠,似乎是那里集聚着的太过浓厚的悲伤和自责,火一般烘干了他的泪水、烧哑了他的喉咙,让他整个人罩在寂灭之中,极是安静,却静得吓人,直到看到棺棂起杠时儿子追着灵车疯狂哭喊的情景,他才恍然醒悟似的,泪水再一次决堤般奔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