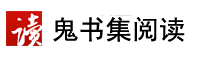第2节
秀才很有眼力价,忙殷勤地递上一颗烟卷。老根叔摆摆手拒绝了,他边用手捻着烟卷边望着远方半山腰处的云卷云舒,自言自语地说:“是有女鬼,可不是恶鬼……”
“不是恶鬼?那难道……是好人冤死的不成?”秀才的神色变了,情绪突然激动起来,他一把抓住老根叔的胳膊孩子般晃动起来,“老根叔,您快跟我讲讲,是什么样的女鬼,为什么要在仓库出现?”看得出,他正在被一种很强烈甚至很悲壮的情绪左右着,已经近乎失去了理智。
秀才的这种表现在老根叔眼里还是第一次,老根叔不禁奇怪地看了秀才一眼。秀才很聪明,马上松开手,情绪收敛地说:“对不起,老根叔,我只是太好奇了,您别见怪,我们文人,都这样。”
兴许是,老根叔想。过去他就听人讲过,说文人写起文章来,会时而哭、时而笑、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暴跳如雷,说什么是进入角色了,感同身受。眼前这个人,应该也是如此吧。
老根叔不再去看这个让他突然感觉有些精神质的男子,他低头用舌头舔了下已卷好的烟卷的接口处,又捻了捻那个地方,然后并不急着点燃,而是把目光再次投向远方,自言自语道:“这女鬼,每时每刻都在,又每时每刻都不在。”
老根叔说着,想着,望向远方的目光不知不觉像蒙上了一层雾。
“老根叔,您……”秀才看到这雾突然化成了一朵晶亮晶亮的水花儿,在老根叔的眼中一闪一闪的。
老根叔转过脸,扯风筝线般地把思绪从遥远的地方拽回来,眼中晶亮的水花上又蓄满了往日的威严与慈爱。他仿佛陡然长了精神般地大声对秀才说:“哪有什么鬼,如果有鬼,也是藏在人们心里的鬼。”他点燃烟卷,猛吸了几口后又大声补充了一句,“秀才,你记着,如果有人说看见了鬼影、听见了鬼哭,那是因为他心里就有鬼!”
不知为什么,老根叔的声音突然充满了悲愤的力量,一颗心,也似乎凝聚了太多的感慨和沉重,在胸腔里忽闪忽闪发泄般摆动着。
面对老根叔骤然涌现的激昂,秀才突然泪流满面,大概是怕老根叔看到,他快速拾起放在地上墙角边的黄背包,只对老根叔摆了摆手,便匆匆离去。
但老根叔还是看到了,秀才半转身挥手时颊上突然坠落的,在阳光下晶光闪亮的一串泪珠。
他越发觉得秀才奇怪了。
第五章 鬼邻的新居
把仓库翻新成住宅,站长满仓的这一决定,从村干部到村民,没有一人提出异议,可偏偏遭到了老根叔的强烈反对。
那是五月的一天,按照满仓的意思,仓库的改建工程开始启动了。这天,两台从兄弟单位调来的推土机,宣战似地扬起推土铲头,轰隆隆地向顽固倔强了几十年的破仓库牛一般抵去。
可就在这时,一声雷鸣般的“住手”的喝斥声像一枚手雷,咣地一下扔在了施工人员面前。人们抬头一看,响晴的天空下,老根叔正宛如一头倔驴,呼哧呼哧地向这边赶来。
老根叔跑到跟前,先是伸展双臂挡住了推土机的去路,然后扔下了一句“不许动,这仓库拆不得!”的话后,又转身移至仓库墙根,怒目圆睁、一动不动,明显摆出了一付“要拆就先弄死我”的誓死捍卫仓库的架势。
按说这老根叔一不是村干部,二不是养牛户,他的反对应该无效,可以不予理睬。可问题是,眼前的情况,硬来肯定要出人命,哪个还敢再动?无奈,施工队只好车灭火、人住手,偃旗息鼓。可又不能撤,只好与老根叔对峙着陷入了僵持局面。
这种架势村人们还没有见过,所以,仓库再一次受到了高密度的关注,不断接踵而至的看热闹的人们迅速在仓库门前形成了一道人墙。
这让老根叔的女儿脸上挂不住了。她接到信儿后,来不及脱下挤奶时被牛屎牛尿溅得星星点点的围裙就跑了过来。
“爸,您这是干啥呀?出的啥洋相啊!”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质问着父亲,拽着父亲的手臂就往人墙外拽。
老根叔甩开女儿的手,嘴唇抖动了半天,然后用一种气愤得近乎颤抖的声音阐述着他充分得出奇的理由。
他说,这么多年了,虽说仓库里常有女鬼哭泣,可谁听说女鬼祸害人了?没有!这说明这个女鬼不是个恶鬼!可如今若把仓库毁了,女鬼没了住处,有可能就会被逼成了恶鬼!到时村人们遭殃谁来负责?……
老根叔越说越激动,倔强执拗了大半辈子了的人,竟然抑制不住感情的冲动,当着几百号村人的面哭开了鼻子。浑浊的老泪和酸渍渍的鼻液,一点一滴从眼角和鼻腔里渗出来,湿漉漉地打湿了人们的心。
村民们哗然了,他们不再看热闹嬉笑,而是开始对老根叔滋生了同情:如果不是对仓库有着什么特殊的情感纠结,这个平日里沉稳老练的老根叔,一定不会表现得如此怪异和孩子气。
人群静了下来。几个刚才还不服老根叔作为的施工队员也都怏怏地放下了手中的家伙式儿,只等着站长满仓的到来。
因为是刚刚上任,住房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满仓暂时只好每天骑着摩托车奔跑于牛村和场部岳父家之间。这天,他风尘仆仆地刚进牛村,就听到了老根叔大闹施工现场的消息,这让他连村部都没来得急进,便一脚油门直奔了仓库。到了仓库,看到老根叔的架势,知道现场说什么也不会有用,便当时下令施工队离开,然后恳请老根叔去办公室谈谈。
老根叔同意了,但直到施工队完全在村头消失他才放心地随着满仓进了村部。
面对老根叔这样一个封建迷信、不可理喻的老顽固,满仓实在是哭笑不得,却又不能把他怎么样,只好好茶好水地招待着、劝说说,希望能好说好商量,和平解决。
满仓的一番诚意终于使得老根叔做出了妥协,但条件是:满仓只能改动仓库的一半儿,另一半不许动。理由很简单:怎么着,也得给女鬼留个栖身之处吧。
满仓露出一丝苦笑,自我解嘲地说了句玩笑话:“这不是让我与女鬼做邻居嘛!”可即便这样,他还是看得出,老根叔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了,何况他也明白,老根叔虽然执迷不悟,但终归还是为了村人们着想,无奈也就点头答应了。
这事,曾一度在村子里成为笑谈,一笑老根叔对鬼神的敬畏荒唐至极,二笑满仓从此要与鬼为邻。没事时,村人就逗满仓:“站长,做邻居可以,可千万别领回家金屋藏娇哦!”
满仓的媳妇秀秀有时也冷不丁跟他开玩笑说:“你自己去住吧,有女鬼陪着你,谅也没人敢跟我抢老公。”
说归说,秀秀还是一心一意盼着随丈夫来牛村定居的。这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自结婚以来,两人就跟娘家人住在一起,这让秀秀一直很渴望自由自在的二人生活。这第二个问题就有些大了。前些日子,农场健康大普查,秀秀突然发现自己的血型与父母有些不符,便心怀疑虑地追问父母,父母无奈,只好将她是捡来的身世倾盘托出。秀秀一时无法接受,为了避免真相浮出后面对父母的那份尴尬,她决定放弃图书馆的工作,跟着丈夫去牛村。
来自老根叔的阻力被解除后,翻修仓库的工程就轰轰烈烈地启动了。不消半个月,一座完整的四合院便以其惹人的雄姿稳稳地盘踞于牛村人的眼中。只是,留下的那半截旧仓库也因此显得更加破旧了,蹲伏在新居的旁边,它就像一个年事已高的老爷爷,在时刻守护着自己的孙子一样。
房子一修好,秀秀就毫不犹豫地随丈夫搬进了新居。儿子小涛因为要上学,只好仍然留在场部姥姥家。
原本破破烂烂的仓库,一经修整,立刻有了家的感觉。屋子虽然不是很大,但按照最新的家居格式间隔了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过去小小的两个眼睛似的木框通风口,也被一个大大的几乎占据了半边墙壁的玻璃窗所代替,每天,阳光大片大片地泼进来时,整个屋子不用生火都暖洋洋的。
住着这样诚心的屋子,又能每天和丈夫在一起,秀秀的心情渐渐好了起来,虽然身世的问题时不时还会像一片乌云飘然而至,可毕竟,到了新环境,这片乌云飘来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也越飘越远了。
第六章 悚人的哭声
搬进新家那天,满仓特意多放了不少炮仗,心想既然都说这里闹鬼,那就多放几挂,驱驱鬼也去去晦气,有鬼没鬼的图个心安也好。
可尽管这样,住进新屋后,满仓的感觉还是跟秀秀的心情大相径庭。
虽说这屋子修整得哪儿都不错,可走进它,满仓的心里就不舒坦,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想到人们说的女鬼,再想到自己第一次走进仓库时屋里依稀留下的有人居住过的痕迹,他就感觉有个人或魂魄什么的东西时刻在屋里的某个角落里窥视着他,或许在怨恨着他的奢侈、诅咒着他的享受,也或许,在愤恨着他的强占和霸道。
总之,这种感觉使他每天都如坐针毡、心神不定,尤其每次想到或看到隔壁留下的那半截仓库,他的脑中就会幻化出一个影子,一个女子,不,确切地说,是一个女鬼在灶边做饭的背影。不,鬼是不吃饭的!那她在做什么,不知道,也许,做饭是挡头,窥视自己,才是真的?
每每想到这儿,满仓就感觉一道阴森森的目光定格在了他的后背上,令他的头皮和脊梁冷飕飕地直发麻。为了摆脱那道目光,每次,他都下意识地揉眼睛、晃脑袋、猛回头,企图消除这一切。可越是这样,那个影子和那道目光就越是挥之不去,萦绕不消。
这样三个月下来,满仓吃不香,睡不好,脸色变得黄蜡蜡的,整个人也瞅着憔悴起来。
很快,村里的闲言碎语水漫金山般地淹了过来:“看来,满仓真的被女鬼缠住了哟,你看他那脸色,那神色,哪是个正经颜色啊!啧啧,看样子那仓库里真的闹鬼吔!”就连媳妇秀秀也经常奇怪地问他:“你干嘛老是揉眼睛晃脑袋的,是不舒服吗?”满仓就说是,可具体又说不出哪儿不舒服,再说这样的感觉也没法说出口,一是怕人笑话,再是怕吓着了媳妇,只好自己忍着。
这天,满仓走在路上,迎面走来一个拿着幡算命的。走至对个儿,算命的用一双透着青光的怪眼瞄了他几下后,突然站下问:“年轻人,最近是不是休息不好啊?可曾看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满仓一愣,继而马上明白:碰上骗钱财的了!便马上否认,雷打不动地说自己是军人家庭出生,从不信神信鬼。
算命先生笑了笑,也不深究,丢下一句“你很快就会信了”的话走了。望着算命先生的背影,满仓无奈地摇摇头,心想,算命的怎么到村里来了,真该管管了。
这天傍晚时,村干部开了个临时碰头会,下班时天已蒙蒙黑,月亮在褐色的云层中还没有升起来。这些年,因为仓库闹鬼的说法,过去离仓库近些的住户都陆续搬走了,仓库也就变成了一座孤房,站在小村的边缘,像一匹守门的老马。
满仓向家走着,村子的中心地带在他身后越退越远了。
快走到家门口时,满仓突然觉得风中似乎多了一种声音,他停下脚步,侧耳仔细听去。没错,是多了一种声音,那声音,衣衣嘤嘤的,像人在哭,而且,像是一个……女人在哭!哭声伴随着夜色下四周荒草鬼魅般摇曳的暗影,如诉、如泣,凄惨惨的,不知源头在哪里,只觉得越来越近。
满仓的头皮一紧,惊觉地向四周看了一下,并没有发现什么。可哭声确实存在着,飘飘渺渺,像在前方,又像就在身后。
满仓不由想起传说中的仓库女鬼,身上的汗毛刷地根根倒竖起来。他来不及多想,三步并作两步窜到自家门口,拉开门一头扎进了屋里。人进屋了,可哭声依然存在,而且,仿佛就在眼前。
是女鬼跟进了屋里?满仓脑中迅速闪过一个念头。他惊恐地抬头,却发现,是媳妇秀秀坐在对面的床上在掩面哭泣。
“没事你嚎啥,吓人倒怪的!”满仓一身冷汗,气急败坏地向媳妇嚷。
媳妇完全不理会他,只顾低着头嘤嘤地哭。满仓气不过,冲过去刚要去掀媳妇的脑袋,却在刹那间感觉,那埋在长发下的低眉顺眼的面孔隐隐约约有些不像是媳妇的脸。
他呆楞了一下,耳边突然响起算命先生最后说的那句话,心中惊惧至极,猛地“啊”地一声大叫起来。
“你疯了,喊什么喊!吓我一跳。”没曾想,他这一声大喊,炕上的女人猛地抬起了头,冲他大叫。
满仓望去,没错,这是自己的媳妇呀!可刚才……?
“刚才是你在哭吗?”他小心翼翼地盯着媳妇的脸问。
“不是我是谁?这屋里就我一个人!”
满仓不敢妄动,他直挺挺地站着,最大限度地转动着一双眼珠在屋里巡视了一番后,心才慢慢地落回到了肚子里,转而大怒:“你闲的呀,没事挤猫尿,谁惹着你了?”
秀秀的眼泪又流了出来:“还不是因为我身世的事闹心。”她仰脸可怜兮兮地问满仓,“满仓,你说我父母当年为什么要抛弃我……”
“行了!”秀秀话还没说完,满仓就烦躁地一棍子打断说,“就别提你家那弄也弄不明白的事了!”
这一夜,满仓翻来覆去,睡意全无。虽然哭声已确定是媳妇秀秀发出,可为什么有那么一瞬间,他会发觉坐在床上的不是秀秀?是幻觉?可幻觉又为什么会那么清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满仓苦苦思索着,他又联想到自从搬进新居后自己的种种莫名其妙的异常感觉,不得不开始第一次认真思考这世上是不是真的有鬼魂存在了。
身旁的秀秀香甜地睡着,发出低低的匀匀的鼾声。满仓下意识地扭头看去,又赶紧将身子向床边挪去,这就使得他和媳妇之间空出了长长的一溜儿空间。显然,这个女人傍晚带给他的惊吓还没有完全散去。
唉,这两天,该去找个看事先生好好来瞧瞧。满仓在黑夜中想着,却不知,不等他的想法实施,一个巨大的变故便已阴影般向他悄悄袭来……
第七章 小村的岁月
如果没有那样的一个黄昏和夜晚,牛村的岁月也许一直都会是安静的、祥和的与富足的。那样的一个黄昏和夜晚,就像是一枚醒目的书签,把牛村的历史隔成了两部,前半部字里行间溢满了祥和,后半部段里段外尽透着恐慌。而要解析那样的一个黄昏和夜晚,我们就必须要从了解小村的岁月开始。
成立了五年的牛村,也许是从业性质的缘故,村貌上暂时还呈现着杂乱无章的状态。
这里没有开阔的场地,凡是空闲的地方几乎都被建上了牛圈、盖上了草棚。村子还没有开始规模性的绿化工作,所以“花如海、树成带”的优美景观还远远不能与之结缘。村子里除了各家各户屋前屋后少有的一些低矮植物外,周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树木,只有村边的几株白杨,与小村格格不入地傲然耸入暖洋洋的天空,却把它们瘦伶伶的影子甩在脚下。
村子还没有什么像样的道路。一条贯通东西的土路上,名副其实地散落着密密麻麻的牛蹄窝和排着队伸向远方的牛羊粪便。晴天还好,走在上面,大不了脚底被咯得生疼一些。雨天就惨了,雨水和尿液和在一起,泥土和粪便混在一处,黏腻腻地无从落脚,偶尔有车进来,多数也是在泥泞的路上失控地七扭八扭后,倏地一下滑进路旁的污水沟里去了。
可尽管这样,这条路仍是村里唯一的一条主路,每天承载着牛群的鱼贯而出鱼贯而入,保持着小村与外界的各种生生相息的关联。当然,也代表着牛村的脸面。
为了保护好这张脸面,村头大喇叭里三天两头地招呼大家义务出工清沟垫路。可牛村毕竟是“牛村”,前脚刚拾掇完,后脚便又有牛群大摇大摆地走过。
这些威武的将军般的奶牛们,迈着雷打不动的四方八步,或走向村外,或踱回村里,永远都是那样的心安理得,那样的一付功高镇主的模样。尤其是在滩肥草美的牧地进行了一天的饱餐后,嘴巴更是悠闲自在地不停地捣动着,发出幸福的刷刷的倒嚼声。宽而粗大的鼻孔也时不时朝天扬起,示威般喷出一团团浑浊的白气。
许是早已洞悉了村人对它们无法割舍的依赖,这些牛儿们对手拿工具,站在村路两侧为它们恭敬让路的清洁工们从来都表现得熟视无睹。它们常常在他们无奈甚至有些祈求的目光中,于几声得意的哞鸣声后,再一次旁若无人地把热气腾腾、大小不一的新鲜粪便洒满一地,把腥臊恶臭、小瀑布般的尿液灌满每一个深深浅浅的牛蹄窝,使那原本干涸丑陋的牛蹄窝转眼间便变幻成晨光或夕阳下一只只饱满的黄黄亮亮的眼睛。
这时,整个村子便会“腾”地弥漫起一股浓浓的潮湿的热臊味儿,惹得那些伏在牛背上、藏在牛耳朵里、挂在牛尾巴上的蚊子、苍蝇、瞎蜢也好像约好了似的“哄”的一声群齐而起,一窝窝、一团团、一簇簇地飞舞着、嗡唱着,并在与浓浓的热臊味儿一起进村后,无孔不入、无缝不钻、无肉不盯,恼得村子里的每个人都时不时地操起身边的家伙式儿,边咬牙咒骂,边用力驱赶。
此时,正忙乎在灶台边上的女人们多数是麻利地解下身上的围裙,或是顺手抓起一件正好放在身边的破旧衣服什么的拼力抽打。男人则多数是挥起自己宽大的手掌,啪啪地打在自己身上,一打就是一摊殷红的鲜血,黏糊糊的。许是牲口多的缘故,这个村子的瞎蜢蚊子比别村的都要大出几倍多。
牛村的特点便在每天的这时暴露无遗,腥臊、恶臭、脏乱、无章、繁杂、忙碌,可,却又乐此不疲。因为这样的小村,却是日渐富足的。
虽然牛村是合并单位,可村民大多数是跟土喀喇打过交道的人。所以,跟过去每年辛辛苦苦侍弄的几亩薄地相比,人们现在母牛挤奶、公牛卖肉,实实在在地盘算、勤勤劳劳地做活,日子竟真的出乎意料地一天天好起来了。
牛村人最爱的就是每月发奶钱的日子。这一天,人们像过年一样,每人手里攥着厚厚的一沓,互相打探着、相较着,以此丈量着谁家的日子厚些,谁家的日子薄些,可不管谁厚谁薄,比比过去,都是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这一天,便也成了牛村人最幸福的一天,人们在场部奶粉厂领了奶钱后,多数会仨一群、五一伙儿地顺便逛逛商场、遛遛集市,除了买些家用,还会给大人孩子买些穿的、戴的或玩的,大包小包喜气洋洋地挎回家,全没有了过去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穷酸样儿。
渐渐的,牛村便成了远近人们羡慕眼红的地方。为了过上牛村人的日子,这些男的、女的、单枪匹马的、拖家带口的人们绞尽一切脑汁托关系、找门路,想尽一切办法到牛村来养牛。于是,原本并不大的牛村阵容渐渐庞大起来,几年的功夫便从二百余户发展到了三百来家,奶牛也从最初的六百余只发展到了三千多头。牛村,就像一棵成长中的树,从此枝干一节节地拔高,枝叶一日日地繁茂起来,牛村人的日子,也越发殷实、越发忙碌、越发红火起来……
这样的日子,对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来说是绝对无法想象和容忍的。可这样的日子,这样的一种繁忙,对眼前的牛村人来说,却是健康的、富裕的、满足的和幸福的,因为在这些曾经承受过太多贫穷和劳顿的人们身上,表现更多的,是缺少眼泪却不缺少快乐的艰辛的隐忍和承受。因为,牛村人的特点和优点,便是擅长用汗水和勤劳、用泪珠和承受、用坚强和韧性,来喂养他们孕育在心里的从来不会死去的梦想。
小村,就这样走着,像一匹忍辱负重的马拉着一长串青青黄黄、厚厚重重、层层叠叠的日子,在吃苦耐劳的村人们的驾驭下,淡定地、有条不紊地向前走着、走着……直到,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黄昏,和这样的一个夜晚。
第八章 隐患的黄昏
这个黄昏,跟往日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
跌落西山的太阳把最后的光芒洒向大地,让山峦有了红色的轮廓,河流有了金色的波澜,一望无际的田野也因渐袭渐近的暮色而有了流动感,越发显得悠远苍茫。而此时,从牛村袅袅升起的银白色的炊烟,也在不着调的风向中,或升腾、或环绕、或弥漫,最终在渐渐变红的夕阳中幻化成了一缕缕金红色的云彩。
六、七点钟的光景,正是该吃晚饭的时候,可在这个村子里,却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
此时,村里的那条唯一的横贯东西的村路,就像一条长长的输送带,正忍辱负重般地把一队又一队的大小牛群,从野外的四面八方传送到村子的各家各户。
多数这个时候,太阳在西边还没有完全落下,月亮就在东边露出了冰凉凉的脸儿。这让路上行走的牛群便滋生出了许多奇形怪状的影子。影子先是高高大大地笼罩在牛群四周,然后越拉越斜、越拉越长,好似每个牛群后都被挂上了一个长长的战车,阵容便一路壮大着走来,在薄雾渐起的暮色中影影绰绰地前行着,像一次军事大转移,颇显壮观。
牛群进家后,各家各户的声音开始涨潮般此起彼伏地泛滥开来。
放牧归来的男人们一边一个一个地往自家牛圈的木桩子上拴着牛,一边高声叫着自家女人的名字。
家里的女人们习惯了早早把饭做好,因为牛群回来后她们要和男人一起,给牲口饮水、喂料,然后挤奶、冰奶,做好明儿一大早交奶的准备。完成这些活计的过程一般大约需要二、三个小时,为了免得做完这些活儿后腰酸背痛再不想动弹,家家的女人们便提前做好饭菜捂在灶台上。
因牧牛的草滩离村子有些小远,放牧的男人们多数都是中午带了饭的。劳累了一天,中午又啃得冷饭,就的冷菜,所以这时灶台上的饭香是挡也挡不住地直往鼻孔里钻。可男人们只是贪婪地吸溜吸溜鼻子,并没有丝毫放下活计的意思。因为他们看到,饱餐了一天美食的奶牛们,此时一个个的ru房正涨得圆滚铮亮,青筋暴露,仿佛吹弹即破。那是他们的钱袋子,他们必须在最关键的第一时间里把他们挤出来,这样牛奶的质量才会更好,才会换回更多的钱票子。
这样想着,家家户户牛棚的灯就一个接一个地亮了起来,闪闪烁烁、光光点点,使整个村子看起来既像挂满了灯笼,又像落满了星辰。
人们在牛棚里忙碌着、吆喝着,人和牛的巨大的影子交替或重叠地映在牛棚的墙上、木桩上,晃来晃去的一会儿长、一会儿扁、一会儿圆。嗤嗤的挤奶声、奶桶碰撞的叮当声、奶牛骚动的低呣声交织成一片,潮水般涌满了整个村子。
这个时候,经常会有牛翘起尾巴,决堤般哗哗地洒下一大泡长长的腥臊尿液,十有八九还伴有粪便从高空坠落,让坐在牛肚子下挤奶的人不得不快速操起身边的奶桶盖迅速将奶桶盖上,然后低着头、闭着眼等待着这一切过去,却全然不顾了尿液和粪便在自己身上留下的星星点点。
这时的牛村人,之所以按着桶盖、蹙着鼻子忍受着这腥臊恶臭的味道,却丝毫不觉得厌恶,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味儿,是他们的命,是他们的福,是他们的日子。没有了这味儿,他们的生活就会再一次回到原点,再一次了无了盼头。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地守护着那只奶桶,像虔诚无限地守护着一桶桶满满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