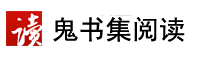第1节
第一章 飘忽的鬼影
这是八月的一个夜晚,月亮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无处不可照及。月光下,一个沉睡的村庄,正宛如一条船,在暗香浮动的薄雾中悠然地摇曳着。
也许是莅临江畔的缘故,这里的夜晚,常会被江边涌来的一大片一大片轻纱般的薄雾笼罩起来。月亮升起的时候,月光和薄雾就会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袭大大的朦朦胧胧的帷幕,令周围的一切轻纱半掩般神秘和生动起来。就像今夜,那漫山遍野泼洒下来的月光和雾,裹挟着田野里弥漫的成熟气息,迷蒙蒙、湿漉漉地浓郁着一种难言的情愫,在村里村外缓缓地流淌着,让人感觉到一个季节的温馨。
夜,就这样静静地,在晚风柔软如歌的拍哄中婴儿一般甜甜地酣睡着。可这样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不知从哪儿挤进了一丝风,手一般慌乱地把雾和月光融合的帷幕迅速地掀开,又迅速地合上,宛如幕后一个人掀开幕布时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又宛如一个人刚要说什么,又突然惊讶地闭住了嘴巴。
果然,这时,在村外一条被踩得溜光的蛇一般扭来扭去的小道上,一个被月光拉得斜斜的、细细的、长长的影子,正清晰地映在河道上,鬼魅般晃晃悠悠地从河边飘过来,直至村口一个房屋前停下。
那是一栋状似仓库的房屋,柔柔白白的月光,以银色的镶边赋予了它明明朗朗的轮廓,使它横卧在梦幻般的雾海中,远远望去,如同一个巨大的礁石。
房屋看似有两个住户那么长,一半亮着灯,一半黑暗着,这就使整栋房屋看上去又像是一只独眼的野兽,卧伏在夜色苍茫中,似乎在警觉地等待着什么的到来。
影子先左右瞅了瞅,然后像长了脚的纸幡般,轻飘飘贴至墙根下。
影子双手抱着一支长棍般的东西,他先是把那东西横握在两手之间,然后半蹲下身,缩伏在亮着灯的那半截房屋的窗台下,伸长脑袋在侧耳探听着什么。影子的个头似乎很高,这就使他半蹲下来的身子显得很笨拙很辛苦,从背后看去,难看得就像一只大大的紧紧贴在墙根的壁虎。
尽管辛苦,他蹲的时间还是持续了很长,以至于刚才因为他的走近而停止了歌唱的秋虫,在厌倦了许久的等待后,终于又不得不重新肆无忌惮地放开了喉咙。
可他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一切,只是于许久的探听之后,开始让自己的身体在月光下怪物般地一寸寸向上长起,直至一个长着两只大大耳朵的圆圆脑袋完全暴露在从屋内透窗而出的明晃晃的灯光之中。
这期间,一片落叶曾飘落在他的肩头上。这也许让他误以为是谁在后面轻轻拍了他一下,于是,他受惊般猛地回过头来,同时一只手牢牢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挡回了那一句几乎要冲口而出的带着惊惧颤音的:“谁?”
那瞬间,月光照在他的脸上,像手电筒突然照到了一张恐怖画。月光和灯光交错映出的他五官的阴影,使他的脸上宛如长满了深幽的眼睛或黑色的小洞,在迷离月色的渲染下,在他怪异举止的衬托中,极显恐怖骇人。
当影子意识到只是一片树叶时,因为紧张和惊惧耸起的双肩又缓缓地塌了下去,想是心里长长地松了口气。然后,他没等月光进一步探究,突然巨人般站起,端起手中长棍般的东西,“咣”地怼进了面前挂满日光灯晕的玻璃窗。
窗上的玻璃“哗”地一声碎了,接着“叭”的一声巨响脆脆地从屋内传出,突如其来的闪电般撕裂了小村宁静、安详的夜晚……
仿佛雷声紧跟着闪电一样,巨响余音未了,窗内的灯就倏地灭了。在片刻的死一般的沉寂后,屋里突然传出了不安的骚动和慌乱的喊声,仿佛睡梦中的人突发了梦魇一般。
影子迅速收回棍子般的东西,狸猫般疾步飞奔到屋子的十米开外,犬一样匍匐在一片荒草之中,并瞪着一双猫头鹰般荧荧闪烁的眼睛,警觉地搜索着四周。
看到四周并没有人来,影子显然松了口气,又竖起耳朵仔细地听起来。大概确定了屋内传出的确实是哭喊声后,影子的脸上露出了阴狠得近乎狰狞的笑容。他抹了一下额头上不知不觉冒出的一层冷汗,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般骂道:“狗日的,别怪我狠,这都是你们逼的……”然后,鬼魅般长身而起,风一样消失在夜色之中……
那晚的月亮许是吓坏了,一头扎进厚厚的云层里,再也不肯出来。越来越浓重的风,也怕这一切惊扰了什么似的,一口吹灭了几颗正沿着云层边缘灯笼般游走的星光。没有了月亮和星星,天空像一把巨大的黑伞,严严实实地罩住小村,使小村马上变成了一幅影影绰绰黑黢黢的水墨画儿。
很快,一场冷泪似的雨乘着风的翅膀袭来,似乎想为被害者悲咽,却无意间掩盖了来自窗内的悲鸣,把世界笼罩在一种苍茫而悲壮的混沌氛围中。
罪恶就这样被黑暗和风雨隐藏了。次日,当天生曙色,人们听到消息,一个个在淡青色的晨光中神色匆匆地朝村口房屋奔去的时候,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太迟了。
这是发生在一个叫“牛村”的一桩惨案:一个年轻的女子,死于一管猎枪之下。
惨案发生后,猜测、议论如潮而至。有人怪里怪气地说:“我就说嘛,这仓库是动不得的!动了就会倒霉!”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咒语般预测了小村的未来。接下来的岁月里,小村接二连三地承受着一些奇异事件的发生和惊心动魄的折磨,就像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孩童,从此变得惶惶恐恐、惴惴不安。小村,也因此被称为——
“怪村”!
我们的故事,要从小村的由来开始说起。
第二章 小村的由来
在中国东北部有一条中苏界河,叫黑龙江。黑龙江的北岸是原苏联一个不知名的小城,南岸则是中国边陲小镇萝北县县城。从萝北县城沿着蜿蜒曲折的江畔向南,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宛如一截尾巴似的綴在萝北县城的身后,因此得名“萝尾村”。
萝尾村不大,也不算小,四十几栋房屋,百十余户人家。
小村的西边和北面,是一片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树林。听老一辈人说,这里原本是一片原始森林,经常有野猪、狍子甚至黑熊等野兽出没。随着后来的开发,林子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薄。小到采蘑菇的山民一天便能圆圆地转个圈,薄得每到清晨和日暮,林子里能看得见密集的晨光和被树木切碎了的斑驳的落日,完全没有了过去的神秘和幽深。
小村的南面,则是一道地势上高出小村许多的山岗,当地人称“南岗”。岗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冢,除了每年清明节的祭祀活动,和成群成片的乌鸦在起飞和降落时发出的呱呱的叫声,这里平时能看到的只有乱草,能听到的只有风声。
小村有着并不多也并不肥沃的土地,却几十年靠着这点薄地过着贫穷但却安安静静一成不变的日子。可八十年代初期开始,这里突然像一个干瘪的气球被挤进了一丝春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改革开放的国策,让这里的年轻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镰刀锄头,一批一批地走出村外追逐梦想去了。
小村的人口结构迅速发生了变化,十几年后,村里已经变成老人和孩子的世界,没有一个年轻男女了。没有了年轻人的村庄显出了一种朽木难得生发般的令人心悸的空虚和脆弱,萝尾村,就像一个没有了发动机的铁牛,建设上再也无法启动。
很快,这里被拆迁了。所有老幼妇孺都按照政策进行了外迁。萝尾村的原址上,只剩下了一个空旷旷的名号和一间破旧不堪的仓库。萝尾村的实体消失了,有关萝尾村的一些不在册的历史也随着人们尤其是老一辈人的外迁而从此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无从考问了。
公元2001年的春天,萝尾村的原址上早已长满了荒草的时候,上面的一个政策,把这个已经独有虚名的村子划归给了军垦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的一个政策,又把萝尾村与该农场下辖一个叫洼子沟的连队合为了一体。
合并后的单位,从事的不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种植业,而是引进了一大批优种奶牛。这些气宇轩昂的奶牛一进村,便给小村带来了春风一般的生机和希望。每天早晨和傍晚,大量莹白莹白的从这些牛硕大的ru房中挤出的“血”,被送往农场新上马的一家奶粉厂。
合并后的单位被命名“畜牧站”,后被俗称为“牛村”。成立后的“牛村”,不仅融合了萝尾村和洼子沟两家的血液,还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的源源涌进。牛村,就像一个混血的新生儿,从此,开始了它漫长的历史行程。
“牛村”坐落在原萝尾村址地上,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过去遗留下来的晒场、粮囤以及一些不适合养牛业的设施全部进行改建。
新行业即将带来的前景,像为早已腻歪了传统种植业的人们注射了鸡血一样,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盖牛棚、挖冰窖、修瓦房,使已破败不堪多年的萝尾村完全焕然了一新,在流水东去的黑龙江畔昭示出一种奇异的气质和崭新的风貌。氛。
昂扬的干劲儿和急迫的心情,让人们充分利用起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旧村资源,整个一个漫长的春天里,牛村都洋溢着一种繁忙欢乐的气氛,唯独村头一个破旧的仓库还在孤零零地闲置着,像一头荒原中的老黄牛,在用尽了一生的气力后,身心布满疮痍地悲惨地病卧着,无人问津。
仓库似乎和村庄的历史一样悠久,因年久失修,屋顶的瓦缝间挤满了残叶积骸,甚至长出了二尺多高的荒草,远远看去,就像秃子头上突兀长起的一绺头发。墙壁的泥皮一碰就会剥落掉渣儿,稍稍牢实点的地方也是绿苔绣织,似乎在醒目地证明着它孤独的站立和久远的存在。
仓库的大门紧闭着,像一张缄默了很久很久紧抿着的嘴巴。门上的一把硕大的铁锁也已被岁月腐蚀得斑驳陆离、锈迹斑斑,早已看不清了原有的颜色,却仍如一位威严的老将军,横刀立马地尽现着它的忠心与职责。
牛村在不断扩大着,村子也日益一日地喧哗起来,唯有这间仓库,仿佛一位被人遗忘了的走失了的老人,徘徊在村口孤独地期盼着家人的寻找。可新人不断地进来,奶牛不断地引进,仓库却仍然不断地延长着它的孤独,备受着人们的冷落,偶有外来养牛户问起,也被人们一句“闹鬼哩”吓得再不敢惦记。
“真的有鬼吗?有谁见过?”随着外来养牛户的增多,总有人似信非信好奇地询问着,不甘心地动着仓库的心思。
“鬼是没见过,但总听到鬼哭哩。像是个女鬼,说不上哪天就会来一次。”有人开了头,接下来大家便开锅一般你一句我一句讲开了关于某年某月某日听到的鬼哭的故事。无所顾忌、绘声绘色、生动骇人的讲述,让仓库闹鬼的故事雪球般越滚越大,直至大过了人们对仓库的**。
其实,这些说得真事儿一样的村民们,没有一个亲自经历了他们口中的鬼事。他们中的一些人只不过是来自原萝尾村的周边,过去对萝尾村的一些历史捕捉过一些只言片语而已,但这只言片语很快就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般烧遍了整个村庄。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有想动用仓库的人便都打消了念头、做了罢。信不信不说,主要都想为了图个清静和吉利。
破旧的仓库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冷落下来,在牛村的边缘凄惨惨、孤零零、阴森森地站立着,继续独自承受着岁月的摧残。
直到有一天,一个年轻人的到来。
第三章 新来的站长
成立后的“牛村”,俨然一个新生事物,沐浴着农场各种优惠政策的雨露恩泽,也在四年的光景中,先后造就了两位站长的高升。
于是,在很多人眼中,牛村,显然是仕途人士一块平步青云的“跳板”。能来牛村任职的人,也都会被认定是一定有着坚实后盾和远大前景的人。
牛村成立的第五年,麦苗从地下还没有钻出来的一天,村里来了个干部模样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便是牛村,即畜牧站的第三任站长。
正像大多数人认定的那样,这个年轻人有着旁人望尘莫及的强大后盾,他的舅丈人是农场现任场长,他也因此在这个农场算是个正儿八经的“皇亲国戚”。可人们并不知情的是,年轻人到牛村,并不是舅丈人所使,而是来自他本人的毛遂自荐。为了能来牛村,他在舅丈人面前表态:他不需要舅丈大人的庇护,他要凭自己的能力干出个样儿来,只求舅丈人能给他一个机会和一方舞台。
年轻人表的这个态,颇得舅丈人的欣赏,认为就凭这儿,这孩子也错不了,便满怀欣慰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给了他牛村这片历练的天地。
年轻人刚到牛村便不闲着,第一天在村里转了一圈后,第二天便在仓库门前停了下来。
年轻人像端详一件古董般,不声不响地围着旧仓库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地看了半天,然后又不声不响地转悠着在周围找到一把看似好久没人用过了的废弃斧头,最后抡圆了胳膊哐哐哐向那把早已被锈蚀得不堪一击了的铁锁砸去。
年轻人突然的举动让跟在身边的两个人颇感意外和紧张。“这锁砸不得砸不得的,砸了恐怕要倒霉的。”其中一人拭图阻挡,却又似乎因为顾忌对方的身份而显得缩手缩脚。
听了这话,年轻人抡起的斧头停在了半空,他扭头望着阻止他的人,奇怪地问:“为什么?”
那人嚅嗫了半天,终于用和村人们一样的语气,向年轻人描述了关于这里几年几月几日几时曾有女鬼在哭泣的怪事儿。该人的嘴巴迅速地一张一合着,说得快而急。因为他知道,这个怪事儿已宛如裹着神秘色彩包装的炸弹,经过牛村人一次又一次百试不厌的投掷和传承,已被验证具有了相当的杀伤力。所以他认为,只要听完这个故事,这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儿,肯定会马上停止他不理智甚至有些鲁莽的动作。
可事情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年轻人没有等他叙述完,便再一次抡起了手中的铁斧,并在砸击铁锁的过程中不咸不淡地听完他的叙述后,不但没有显出丝毫紧张和害怕,反而头也不回看也不看他一眼地说了句“是吗?那又怎样,还能放出鬼来不成?”说完,便不再理他,而是扔下刚刚砸开的铁锁,拍了拍粘在手上的铁锈,伸手去拽仓库的大门。
年轻人长得已够强壮,使的力气看着也不小,可大门只是在吱嘎嘎发出一阵痛苦的**后极不情愿地忽闪了两下便执拗地归回了原位,刚刚开启了点的门缝也随着大门地停止忽闪而一闪即逝。
很显然,年深日久的闲置,仓库门已被结结实实地锈住了。
“还不赶紧过来帮忙!”年轻人并不甘心,他有些恼怒地喊上在旁看得胆战心惊的两个人。三人咬着牙,使出吃奶的力气,半晌,才“嘿”地一声哐啷啷拉开了沉重的大门。
门一打开,潮湿阴冷之气便扑面而至,猛烈得巨浪一般,险些把站在门口的三人打个跟头。三人不禁本能地退后两步。年轻人更是眉头一皱,很明显地迟疑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抬腿跨过了门口那道木制的,已被老鼠蛀虫啃得参差不齐从心里往外糟透了的门槛。
仓库里面,白花花的灰尘铺天盖地。顶棚上,是一串挨着一串的灰掉掉,一张接着一张的蜘蛛网。顶棚下,是厚达数寸的毛茸茸的尘被,严实实地盖住了屋里的所有物件。
年轻人在屋里慢慢地走着,看着,鉴别着还依稀可见的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
一个简易的铁桶改制的火炉,笨笨地蹲在屋子正中央,像只委屈的灰头灰脸的小兽,两节铁皮围成的烟筒被焊接成直角,从窗户上方的洞里通向窗外;墙边窗台下是一个沙土砌成的灶台,灶台上散落着一个饭勺、一把锅铲以及一只干瘪的炊头已被磨得平平了的炊帚……
这些东西在多年来集聚的巨大灰尘的掩埋下,只剩下一些边边角角还露在外边,这使整个屋子乍一看来,就像是被蒙上了一张大大的白色熟料布,而熟料布下面的东西,又不甘心就此埋没似的用自己最锋利的部分顶钻了出来,仿佛要以此具体鲜明的形式告知来人:
这,是一个曾经有人居住的地方,而且,居住的时间还很长。
年轻人在屋里走动着,环视着,不时地摸摸灰尘下的这个东西、那个物件,同时漫不经心地似自言自语又似对身旁的人说:“这哪里有什么鬼,分明以前就有人住过嘛!”说话间,又突然扬手啪啪啪使劲击打了几下矗立在屋中央的粗大房梁,一阵灰尘便雪花般自上而下飘落下来,许是年深日久,又无人清理,灰尘钻入人嗓,竟辣蒿蒿的有些呛人。
年轻人咳嗽了两声,看房梁和屋顶并没有因为他的击打而产生丝毫晃动,脸上显出一丝满意,说:“这样吧,这仓库收拾收拾,可以解决两、三家养牛户的牛棚问题吧!”
身旁的两个人不禁面面相觑,脸露难色。其中一个嚅嗫着说“这,恐怕没人敢用吧,因为,养牛户们都听说了这儿闹鬼的事儿。”
年轻人皱了下眉头,并不坚持,而是寻思了一下说:“那就收拾收拾我来住,安排给我的那间学堂给村民做牛棚吧。”说完,两手互相拍了拍灰尘,走了。只剩下两个目瞪口呆的人和一扇大张着的、嘴一般的仓库大门在春日的阳光下仿佛欲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这个年轻人,就是牛村,不,准确地说,是畜牧站新上任的第三任站长,姓铁,名满仓。
下文里,我们就简称之为满仓吧!
第四章 奇怪的秀才
新站长砸了仓库门锁的消息像一阵风,顷刻间传遍了整个牛村。人们惊叹着,纷纷放下手中的各种活计,争先恐后地向仓库涌去,都想看看这个据说闹了几十年女鬼的屋子里到底有着怎样的奥秘和玄机。。
这一刻,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便像千军万马掠过,淹没了整个村庄。
仓库像一个新开发的景点,涨潮般迎来了几十年来最热闹的时刻,人们一波一波赶集似的,俩俩仨仨地前来,三三五五地离去,络绎不绝。几天后,许是并没有发现自己想要发现的东西,人们便像看腻了一幅旧画,又退潮似地一退千里,再无兴致了,只留下了一些只言片语,很快也被大风刮跑了:
“就是一个仓库嘛,竟是些破烂东西,哪有什么女鬼,胡说八道呢吧!”
“这可不一定,无风不起浪的,谁知道这里面以前发生过什么呢?”
“看着里面过日子的东西还很齐全,想来住的是一家子人吧!”
……
那么仓库里面究竟发生过什么?又究竟与谁有关系呢?现在的牛村,恐怕已无人知晓。毕竟,岁月走得太远了,就像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只留下一个隐隐约约的背影,让人无法辨认,或已辨认不清。而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也在外迁之后,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聚”与“分”的重新组合后,而再也寻不见了踪影。
所以,看热闹的人们在一哄而散时,几乎表达了同样的一个意思:“唉,该干嘛干嘛去吧,闹不闹鬼儿的跟咱又有啥关系呢?”
于是,喧闹了几天的仓库门前,很快又“门前冷落鞍马稀”了。
就在人们淡漠了仓库话题的时候,再次被冷落下来的仓库却迎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的光顾。
男人走进仓库,环顾了四周后,在满是厚厚灰尘的破桌子上看到了一支钢笔。钢笔被灰尘紧紧包裹着,只有和桌面接触的那边还保留着原来的颜色。男子拿起笔,轻轻吹去上面的灰尘,用手细细地摩挲着,端详着,背向大门的肩膀有些轻微的压抑的颤动。
男子带走了那支笔,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会对那样陈旧的一支笔如此的看重和珍爱。也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
对这个村子里的人来说,这是一张陌生的面孔,除了老根叔。
老根叔六十二、三岁的年纪,虽然长得不够厚实,却看上去少有的硬朗,除了一绺胡须有些灰白以外,整日里是满面红光、精神矍铄。
老根叔自老伴去世后就住在女儿家,平日里没什么事便东瞅瞅西逛逛,帮这家整点啥,给那家弄点啥,要不就上山采点草药什么的。一次上山采药时,恰巧看到男子举着一部相机咔嚓咔嚓对着树丛照着什么,两个人就打着招呼相识了。
老根叔认识男子已经两个年头了。男子不知从哪里来,只说自己是写小说的,在南方一家报社工作。还拿出过一张名片给老根叔看。老根叔出了一辈子苦力,虽说识字,但毕竟对文字不大感冒,所以对那张名片瞅也没瞅,只看男子长得文文弱弱的,一副秀才样,便就信了,也不问他的名字,就直接呼了“秀才”。
秀才不知住在村外什么地方,他不说,老根叔也不问。秀才每次来都没有准时候,也不见其他人,就找老根叔讲故事。而且听得也认真,每件事都记在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本上,听完后,不管在不在饭点上,背起那个黄不唧唧的背包就走。
老根叔给秀才讲过很多故事,具体都是些啥,他也记不得了。秀才给他的印象很沉稳,不急不躁的。可这天,秀才从仓库出来,找到老根叔突然问:
“老根叔,仓库里真的有个女鬼吗?您给我讲讲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