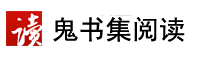第47节
我运功将阿菜与我的元婴从各自体内逼出,看着两者逐渐融为一体,然后想都不想地塞进了他的嘴巴里。墓室中金光四溢,顷刻间他便醒了过来。他凝视着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瘫在地上挣扎着笑道:“不是所有事情都有原因的,想了便做了。我知道自己无法改变难以共生的结局,但是至少左右了我们在一起的过程。”我指着当年那伙人进来的盗洞说,“走吧,你本就属于外面,我只是恰巧醒来,有段故事拿来回忆已经足够了。”
阿菜满面凄凉,左手轻轻一挥,数块巨石挡住了那最后的出口。我已无力说话,只能用疑问的眼神看着他。他说:“还记得玉菩提的传说吗?那其实是我编的,瀛洲人从未相信过那种花的存在,他们相信的是财富与权力。我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但现在我醒了,因为我找到了那种花。”
我突然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疲惫在身体里弥散开来,视野里是无尽的深渊般的黑暗,我在这片漆黑中踽踽独行,在即将失去意识的最后时刻,我听到有个声音突然从头顶上传来。
只听他呢喃道:“那朵世间最美的花——玉菩提,它就开在你的心里。”
蜃楼翡
文/云海
天下间的奇珍古玩,无不是先天汇聚了天地间灵气,后天又经妙手匠人呕心沥血的雕刻,才成就绚烂夺目的光泽、令人咋舌的身价。而一件奇珍异宝的归属,除去天时地利、高价购买外,更要看你命中有没有得到宝贝的福泽。
从古至今,就不乏为了稀世奇珍而来往奔波的猎宝师,而他们,更多是靠运气和眼力。
九月初八,宁州。当地首屈一指的富绅贾大人府上,已经持续进行了三天紧锣密鼓的招魂仪式。邻近的一户人家终于受不了贾家闹鬼且会影响周边风水的传闻,整家仓皇搬离。大街小巷里关于贾府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闹得整个宁州街坊人心惶惶。
市集茶楼之中,几个闲汉正唾沫横飞地谈论贾府之事,原来贾老爷在自个儿家忽然昏迷不醒,已经七天七夜,请了几位大夫药石无灵,又请了好几位神婆道士,但贾老爷就是醒不过来。
临窗一桌落座的是位白袍男子,姓白名景行。他掌心端着细瓷碗,正品着茶,对几个大汉的吹嘘喧嚣声也不言烦躁,只是静听着,将视线远眺向窗外。对桌还端端正正坐着一个灰衣少年,比白景行年长几岁,瞧衣着身份似是侍从。白景行将视线转回,饶有兴趣地对灰衣人开口道:“陆恒,你说真有人一梦不醒吗?”被唤作陆恒的人斟酌了一下,方回答道:“人若是一觉不醒,身体没有食物饮水补给,是支撑不了多久的。黄粱一梦不醒,终是虚妄。”陆恒知道自家少爷喜欢听那些山野的奇闻趣事,不急不缓给少爷续上了茶水,顿了顿道,“贾赫在宁州算是富庶一方了,听闻他也喜欢收集古玩字画。只是少爷此番倒是不巧,碰见他病入膏肓,怕是见不到那些奇珍宝贝了。”白景行倒是不以为意,细斟慢饮清茶之余,莞尔道:“我倒觉得此事蹊跷,天下哪有这般古怪的病症,你我何不去贾府看看。”
原本富丽堂皇的贾府深宅,现在贴满了各种黄纸符咒,几个蓝衣道士还在低头默念书写着古怪的咒语。内堂里,三四个妻妾围着床榻上的男人哭哭啼啼。那榻上脸色灰暗、双颊消瘦的人乃是贾府之主贾赫,已经不复昔日大腹便便的圆润模样。此刻他呼吸微弱,除了尚能灌服一些参汤吊命之外,一点儿苏醒的迹象都没有。默然看护的贾夫人重重叹了一口气,将目光转向案桌上一尊翠绿流光的翡翠雕件以及百宝阁上各式古董玩件,这些年贾老爷收集了不少古董,很多是从盗墓贼手里周转来的物件。贾老爷乐此不疲地把玩这些珍宝,自从在南诏边境收来一件稀世翡翠后,更是干脆搬到了书房住,只为能整日和古董相处。
贾夫人暗自寻思,以前听人说,盗墓得来的物件都是给墓主人陪葬的,物件在地底下吸的都是去世人的气息,如果天天把玩,原本属于地下的那些物件就会来吸走活人的气息。贾夫人越想越惊骇,望着昏迷不醒的夫君,终于咬牙下了定夺道:“来人,把老爷这些古董全部收拾了,集中到后院。太阳落山之前,统统都烧了,一件也不留。”身边小妾目瞪口呆——原本还打算老爷死后分些家产,现在如果这些字画古玩烧了,自己能分到的那份不就少了许多?一人不由得站出来道:“这些都是老爷花大价钱买的,都烧了,老爷醒来不得大发雷霆?”贾夫人横了她一眼,道:“如果老爷醒了,那证明烧了、砸了这些东西还是有用的。要是全烧了也没用,那就让它们随老爷去吧,也不枉老爷宝贝它们一场。”众小妾还想说什么,被贾夫人环顾的一记严厉眼神给剜得咽了下去。
未时刚过,贾府门口来了客。这可是新鲜事,这几天大家对晦气的贾府都避之不及,本来人声鼎沸的富绅之家,现在哀哀戚戚门可罗雀。只见四匹白马载着一辆宽敞的马车缓缓停住,来人正是白景行。他身后跟着一个高挺佩剑的灰衣侍从,便是陆恒了。白景行祖上世代经营古玩物件,拥有十几家当铺,也是闻名两江的世家。白景行自小喜欢收集奇珍宝贝,游历四方,是一个以眼光犀利、见闻广博驰名的猎宝师。他身边的侍从陆恒,武功极好,性格忠耿。
白景行并不在意世俗眼光,自言乃是贾老爷旧友,听闻贾老爷有恙特来探望。按规矩拜见贾夫人,一番礼节客套慰问之后便去了贾老爷昏迷的书房。本想找到些致人昏睡的线索,但一番查探之后也是无功而返。眼见几个家丁正在后院劈柴架火,旁边放着一堆古玩字画掩着幽幽一抹碧光流转。白景行走过去,慢慢拾起来发现是一尊雕工精细、结构繁复的翡翠,约大半个手掌大小,翠绿色泽中带着一团一团的墨色,下面还连着特意打造的金丝楠木底座。翡翠被多层镂空雕刻成一座城门的样子,一层一层十分逼真,甚至还有戍守城门的将士,不过寸许大小,一脸坚毅表情却栩栩如生。
白景行眯了眯眼,将翡翠对准阳光,翡翠内一汪盈盈的赤色不安地缓缓蠕动。他不禁微讶皱眉,又仔细对光研究了下,那赤色不似活物,倒像是凝结了久远的血色雾尘。白景行微微一笑,对身边的家丁道:“快去通知贾夫人,我想贾老爷的病有救了。”他用掌心摩挲着那方翡翠,似有所悟。莫不是这宝物也有灵性,知道自己葬身柴堆的命运,才幽幽发出光亮,引识货之人找到自己?
原本一脸哀戚的贾夫人,听闻自家夫君有救了之后急忙赶来,白景行瞧着贾夫人面容枯槁,不由得心生不忍,取出翡翠直言道:“贾夫人,我在柴堆发现了这个,瞧着成色乃是产自南诏边境的玉石翡翠,经巧匠呕心沥血雕刻而成,名曰‘蜃楼翡’。”白景行将翡翠城池放倒,城楼上的牌匾依稀刻着“蜃楼城”三个字,笔画细如蚊足,但仍清晰可见。白景行沉声道:“珠宝玉石一类,都是山川河泽里的矿脉深埋地底,经过几千万年孕育而成,岁月一久,就得了天地间的灵气。更何况玉石翡翠,本就有通灵之说。”他抚摸了下那墨绿幽深的蜃楼翡,“这蜃楼翡怕是给历代死守城池而战死的将士们殉葬用的。他们生前死守国家城池,死后仍不瞑目,是故用翡翠打造了一所蜃楼城池让其灵魂安息。贾老爷怕是不慎从盗墓者手中买回了这块殉葬用的翡翠,招惹了冥怨。”
贾夫人听得目瞪口呆,急忙问道:“白公子可有办法解?若是夫君能平安醒来,贾府上下愿以千金相赠。”白景行眉峰稍扬,正色道:“戍国将士皆是英灵,并非有意缠身,只需用铜钲敲响,让战士们知道战争结束就行了。所谓‘鸣金收兵’,敲的正是这铜钲。至于千金,白某并非乘人之危之人,若是能让贾老爷安然无恙,作为朋友也就欣然而喜了。只有一个不情之请,贾老爷昏迷是和蜃楼翡有关。古董字画无辜,世间古物本是稀少,还望夫人手下留情。”贾夫人也是通情达理之人,再者若是贾老爷醒来,看到他的宝贝全都烧了,只怕会再昏过去,当下欣然应允。
次日白景行布置好道场,差人烧香祭奠,鸣响铜钲。当日天色倒也奇怪,自焚香起,天边就聚起了浓厚的乌云,层层蔽日却又不下雨。白景行微扬下颌,指端拈了香灰一搓,轻啧一声道:“魂魄之气积压得紧,香灰都潮了,还得让陆兄出马,啸一回胆,不然待这积着阴气的雨落下来,就糟了。”陆恒得令,迈步上前,目光对着香炉凝定聚敛,抬手“锵”一声拔剑出鞘。啸胆,乃是对付怨气重的灵祟的一种方式,意在用武镇压怨灵。负责啸胆的人必须八字纯阳,身上所带罡正之气极重才可以。
陆恒持剑在手,臂力满贯挥舞剑锋,四十来招后,一声朗喝,剑势如行云流水而涌,陆恒迎风洪亮发声:“阴阳有别,天地各分。礼香一捧,驱雷奔云。庶人贾氏,误入歧途。今将召颂,勿使相扰。来往不侵,各自相安。开旗急召,不得稽停。——急急如律令,去!”剑锋划过处,一招神全气足的“万岳朝宗”,剑尖长锋与铜钲交击,铮然有声。白景行再去看香,炷香尖头覆盖的灰已然脱落,香火也盛了五分,不现之前的萎靡气象,便道:“成了!”陆恒点了点头,扬手冲香炉案上撒一捧丹砂,收剑立于白景行身后。
午时三刻,贾老爷便悠然转醒,贾府上下皆大欢喜。贾老爷尚自惊魂未定,自言去了一个奇怪的城池,自己本无意闯入,只是走着走着到了城墙口。正眺望着夜色中的城头,突然城门乍开一线,一路持炬的铁甲军自城门涌出巡查,发现“行踪诡异”的自己。这队军士见贾老爷无户籍,又说不出自己打哪儿来的,纷纷肃容拔剑。贾老爷随后就被扣到内衙牢房审问,一路坐着囚车过街道,看着那琼砖玉瓦不似人间,且终日阴天没有太阳,出奇地冷清萧瑟。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兵将,高悬的五彩灯笼被血迹溅污,又被枪戈扫至地上跌个粉碎,街道两侧的雕花牌匾也被踩踏得零落不堪。贾老爷歪着头想了半天,道:“后来只听得那里的将士说什么鸣金收兵,查到自己的身份却非奸细,亦非此界中人,打开城门,命我回来的。那个地方好像叫作……蜃楼城。”
后来贾夫人把蜃楼翡的来龙去脉讲了,贾老爷心惊不已,浑身上下瘦了二十来斤,但犹自庆幸自己一条老命是保住了。他感念贾夫人不离不弃之忠贞,遂愧疚遣散了三位年轻妾室,分与足沛金银让她们自谋生路。再得知自己能回魂全靠白陆二人,定要重谢白景行。白景行却道,就只赠我这蜃楼翡吧。贾老爷正巴不得,当即像处理烫手山芋一般送给了白景行。白景行含笑而受,请了白马寺的高僧给翡翠做了几天道场,又亲自去古旧的南疆烽火台遗迹前洒酒祭奠,安抚了翡翠楼城里的将士英魂,然后便安安心心地将蜃楼翡纳入了自己的收藏里。
裳战
文/吴辙
汽车在途经一个小镇时停了下来,司机带着一大箱工具钻进了车底。过了一会儿,他灰头土脸地爬出来,宣布我们至少要在一个小时后才可能重新上路。
这个小镇自然不是我的目的地,而我在返回省城时将会走另一条路。也就是说,可能这是我此生唯一一次经过这个小镇。小镇不大,我想一个小时的时间逛完一遍是非常充裕的。下车后,只见一条石板铺成的路伸向远处,这石板年代久远,早已失去了颜色,坑洼起伏也比比皆是。两旁房屋虽大多是新近盖成的,但间或几间至少可算古稀双庆的旧房,使小镇有一股掩不住的古意。漫步于这唯一的街道上,倒也颇有意趣。在临近大路的小摊上吃过一碗素面之后,我发现镇上的杂货店就在不远处的几间老屋中。左右无事,我信步踱了进去。
老房子采光不好,屋里的灯泡又几乎是负度数,比没开还暗,只能勉强看清东西的轮廓。好不容易适应了昏暗的光线,我环顾四周,只觉这里确实无愧于“杂货”二字。地上是堆叠如山的书籍,毛巾、香皂等日常用品杂乱无章地摆在已拥挤不堪的货架上。剩余的空间则被恒河沙数般的文房、牙雕、拓片、瓷器、摆件们霸占,只有一小块地方勉强够我落脚。
我奇怪道:“贵店还经营古董生意?”
“小店哪有什么古董,不过是些不值钱的玩物。我年轻的时候也算去过不少地方,入手过几件东西,既然你有兴趣不妨看看。”店主是位老先生,戴一副眼镜,气度做派让我联想起以前私塾的先生。
我对古董有一定兴趣,但说起鉴赏就一窍不通,也只能随便看看。突然,我的目光被柜台旁一个半人高的青花瓶子里的一片红色布角吸引了。我有种奇怪的感觉,似乎瓶中之物该有一番繁华俗世风貌。勉强绕过各种杯盘碗盏走上前,我抓住那片布将瓶里的东西抽了出来。
那是一件大红色的彩绣宫装戏服。
材质顺滑的戏服像流水一样从手中滑过,入手分量沉重,显然是上好的丝缎裁成。如果我少得可怜的知识靠得住的话,这应该是一件民国时期的戏服。那个时代由于条件所限,难以刺绣出繁复艳丽的纹饰,大多数戏装上的花纹都由工匠绘制而成。而面前这一件却以彩绣和半金绣,精细地刺出了一对五彩凤凰和各色花木,花样之复杂繁多难以尽述。裙子上缀有的无数彩色绸带则更加绮丽飘逸。虽已历经百余年,色泽褪去不少,甚至有些黯淡无光,但全部展开之际,这阴暗的小店似乎也被它的光彩照得亮堂了几分。可以想见当年那位梨园名家身着它舞态生风之际,是何等雍容华贵,艳丽辉煌。
我道:“这想必也是老伯无意间偶得的珍品吧?”
老先生道:“那倒不是,我记事的时候就已经在这宅子里见过这身行头。据先严说曾属一位名伶,但一直无人加以重视。我想它价值是有的,不过绝非什么珍品,你想要可以便宜些拿去。”我心说看这么随随便便的态度,估计地位与一块抹布相差仿佛吧。不过他开出的价格确实不算高,我虽没指望能捡到漏,能买来陶冶情操也不错,还是称谢买下了。
收起戏服走出店门,我回到车上。司机的修理已基本结束,我们又踏上了奔波之路。
回到家后,我在阳光下重新将它展开,细细欣赏,缓缓抚摸,恍惚间只觉身边西皮流水,有板无眼,一个粉面朱唇的女子着宫装盈盈走出,念一句韵白,甩两下水袖,倏忽间又转身离去,留了一地清韵。
又过几个月,一个喜好收藏的朋友不知从哪里听说我新得了套戏装,执意前来见识一番。我推辞不掉,只得勉强同意。没想到他来的时候,居然带来件黑色旧大衣。
“古代有‘斗茶’的雅趣,咱们不妨师法古人,来一场‘斗衣’,比个高下,如何?”朋友笑道。
“你未免太看得起兄弟我了。真有好东西能到了我手里?”我苦笑道。
“做人嘛,最紧要是开心。要的就是玩个高兴,何必太当真呢。”他兴致勃勃,港剧台词都冒出来了,显然心里想的跟这番话是全然两套。
我叹了口气。票友怕戏痴,我六根清净,就是耳根不净,要是不尽早投降估计得被纠缠半辈子。走进里屋取出戏服,我忽然觉出它在轻轻颤抖,好像正为什么事而激动。我摇了摇头,就算明知要被碾压,我也不至于因为比个衣服而紧张到心慌手抖吧,果然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啊。
朋友早已把他那件宝贝大衣拿出来铺到了桌上。“这件大衣和你那件一样属于民国时期,贵在做工精细,用料考究,一定出自当时最出名的师傅之手,够资格穿它的,不是军阀,就一定是日本高官……”他正在陶醉地滔滔不绝,那件大衣突然从桌上一跃而起,打断了他的长篇大论,气势汹汹地直扑我手中的戏服。而戏服也突然从惊慌失措的我手中飞起,躲开了大衣的扑击。大衣一击不中,转身又上,如饿虎扑食般凶狠,大有将戏服撕成片片碎帛之势。戏服似乎已处在大衣凌厉的进攻笼罩之下,全不还手,不过进退趋避倒还从容不迫,甚至有几分舞台上翩然而舞的样子。我和朋友终于从目瞪口呆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急忙蹿进厨房,把门紧闭,隔着玻璃看着这场搏斗。
两件衣服的相斗越来越见猛恶,戏服渐渐已呈弱象,躲闪已有些不灵。眼见大衣就要得手,戏服突然起舞,姿态回旋,袖舞翩跹,满室顿生旖旎之感。然而长袖舞动之际,我隐约感觉似乎什么无形之气从袖中逸出,原本飞扬跋扈的大衣忽然委顿在地,随即居然灰飞烟灭了。而那件戏服看上去好像是任务完成,“瘫”在地上也没了动静。
我们待客厅中尘烟散尽后胆战心惊地出来,拾起地上的戏服,回思刚才性命相搏的恶斗,心中犹有余悸。
自此之后那戏服再无异动,我才慢慢收起了畏惧之心,打消了把它一把火烧掉的念头——不管怎么说也是花钱买来的东西。我不是个执着的人,这件事虽奇怪,但既然无法追究,也就作罢。
几年后,我又独自到外地出差,借宿在一个老人家中。老人见多识广,儿女又不在身边,突然有了听众自然十分高兴,与我言谈甚欢。是晚我们小酌了两杯,乘着酒兴我把这件事说了出来,料想他必当作齐东野语,一笑了之,权作下酒之馔。没想到老人听毕沉吟了一阵,道:“你知道名伶李含玉最后的去向吗?”
我摇摇头。当年的李含玉堪称色艺双绝,其他演员连作拱月之星都是极为难得之事。但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何况李含玉这样的名伶。他若愿意,飘然而来,忽然而去,来去之间完全无迹可寻啊。想着心中突然有点儿小激动,升起一念,莫非菩萨长眼,李含玉的戏服竟真的到了我的手里?
老人道:“李含玉最后不知所终,此事究竟如何,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坊间传闻倒是不少。我几十年前听到一个,你若有兴趣,就说与你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