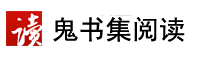第50节
两人轻快地交谈,把独木舟系在一起,几乎是弯腰在荷叶下穿行。
飞廉的身体很好看,柔和、黝黑,肩膀上刺着环形鸠鸟,头发如溶去杂土后在水中舒展的茭白根须。少年也禁不住袒露出筋肉,在没有母爱的疯子一般的生活中,他就像无拘无束的小鸡,无数次跨越边境,享受不同山坳中折射的斜阳……
一条水蛇在船头游弋,他们决定跟着上前看个究竟,结果驶入一片枯木林。接近了句乘山的水下掩体,异常阴凉,两人游了会儿泳。潜进坍塌了一半的隧道,那里在二十年前发生过战争,现在已了无痕迹。
……虚假的秋天,越国公子结束了漫长的流放。
为迎接他的归国,句乘山召开盛大的晚会。公子允常站在年老的大臣身边,穿着碎绿的衬衣,耳边垂下泪形玉佩。这大臣是个老色鬼,同时又慈祥风趣,丝毫不让陌生的公子与陌生的臣民之间,感到一丁点局促。允常垂着头,微笑着,仿佛羞涩的少女,他正处于这种美貌的最后巅峰,似乎坚信能为人所爱。
就在刚才,大臣把他介绍给大家之前,有人恰好挡住允常的视线,使他看不到政敌们的举动,无非宴会的狂欢……
允常的视线在非自然光中搜索,最后停在大厅另一边,飞廉似乎正被人督促着。也许是催账人,催账人越说越激烈,也许有关亡妻的葬礼欠款,失败的男子,甚至无法保障妻子体面地死去……众人的目光追逐允常的航线,抵达这名年轻侍卫。大厅万籁俱静,众目睽睽,犹如层层火焰。飞廉怔了一下,回溯直通航道,向允常报以一个微笑,微笑与微笑之间,仿佛流水中的倒影。
素昧平生的越国小公子,素昧平生的楚国侍卫官,他与他只跳进湖水一刻钟,因为太阳把他们烤得发烫。就在那一刻,句乘山成为他们的林中空地。飞廉的眼,没有失明的右眼,曾在那样的阳光下发光。就在那一刻,在句乘山的另一边,那位绝望的妻子。正不为人知地死去,如果飞廉不与允常相遇,他也许能及时阻止……经过那么漫长的夏天(从三月到九月),他们的畅游仿佛才刚刚开始。
END。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三日。
第五集 越君允常及其宫廷 第二节 花塍
允常与飞廉经过漫长的旅程,在海雾突然散去时,听见歌声。
飞廉放心地睡在车厢里,因为他不会驾车。允常擅长驾车、射箭、算术等贵族活动,飞廉则擅长允常所不擅长的,他们彼此互补……在海雾的那一头,少女们在歌唱跳舞。
他们俩看着少女们,宛如做梦一样。
飞廉走向最美丽的那名少女,她一直在默默凝视他,等待他上前邀请自己,允常则默默凝视着飞廉走进少女的视野。
他们过去几天的逃亡已告一段落。
他们第一次较量结束时,允常蹲在河边清洗衣裳上的污迹,飞廉则在折腾马车。这是卫队长的责任,责任和菜单,是他们最厌倦的两件事。
他走过来,蹲在允常身边。允常只是稍微侧头看他,他轻轻撩起允常满头的卷发,抚摩他的耳廓,拉了拉他的耳垂,然后把食指和拇指撮着凑到他的眼前——那是允常遗落的珍珠耳环。这个轻率的举动后来一直重现在允常心中,连同之前的流放,允常唯一一次没游过海峡,因为水母刺中他的腿而半途折返,在海滩上飞廉为他拔去腿上所有的刺。那种无声的喁喁,那种阳光下的表露,仿佛将爱意大白天下,一直是允常期待的——有人可以公开地爱他。这是他日渐零落的长久回忆,必须隐藏的回忆,由于过于甜美而变成了剧痛。
这时一个更小的姑娘凑近允常,问他,“你们是兄弟吗?”
“嗯?”允常不知该怎样回答。
“她是我姐姐。”少女指向飞廉的舞伴,“你同我跳舞吗?今晚你们可以住我们家。”她非常年少,额头和脸颊涂着蓝色的颜料,这是非常愉快时少女所抹的标记,非常清爽非常健康,她把允常也拉进舞圈。
雾又湿又冷,少女踏在鲜花盛开的田塍上,头发贴在允常失落的脸上,遮住了他的视线。
这是距离越君允常加冕典礼……一千七百天,距离飞廉死去……一千七百八十七天的野趣。
此后的一千七百八十七天,允常猜测,飞廉对他的态度是不停地补偿。因为飞廉不该占他心灵脆弱的便宜,就像一个负心汉不停地送一个已经不为所爱的女人以礼物,希望能迅速弥补她心灵的裂缝从而更快地抛弃她。他只是飞廉生命中的匆匆过客,谁也不想断送前程而处理不当,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国籍、他们的责任和情感比阡陌更破碎支离,谁都感到以后双方都不会满意,也不会得到幸福。漫长的旅程浓缩为一支短暂舞曲,起舞的清影像火花一样噼啪作响,被践踏的恋歌与花塍,只能任其忧伤。
END。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日。
第五集 越君允常及其宫廷 第三节 艅艎
艅艎,也称作“余皇大舟”,是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大型战舰。吴国曾在太湖制造每艘可容纳战士与水手共八十人的大船,北上远征齐国,南下攻克越国。要知道,两千年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他所驾驶的帆船也只有四十九名船员。也许,古代中国人的航海能力,一直都超过我们的想像。
允常对父亲的印象是听来的。姐姐说,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余皇大舟,就用小刀子去刻它的吃水线……这说明他们的父亲被吴国人打败了。
后来的吴越争霸,允常把三十艘快艇的赶制托付给商人,谁造得快就能获得三年免税,他把战争变成了商业的艺术,即使这样也没能自我挽救。吴王叩开了越国的海防,掠走大批人口和财富,在那个遍地野兽比人类更多的公元前,人的价值超过土地——被俘虏的人群中,有越君允常的亲属、仆从、普通民众……还有他最心爱的卫队长飞廉。吴王为了羞辱允常,砍掉飞廉的腿,铰光他的头发,烙上奴隶的编号,让他看守余皇大舟。
总之这一段轶事和允常没什么关系。
这里要讲的是吴国最年轻的整备舰长——余棠桥下。他十四岁时,就能站在战舰龙骨里把麻丝和油灰填充进甲板缝,为造浮桥毫不犹豫地跳进冰水。吴王发给他们很多防冻膏,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年年冬天去打仗,他们还是满手冻疮地打败了楚国人、齐国人和越国人……总之余桥棠下非常严格地自我修炼:即使下雪天也用冷水洗澡,与士兵一起操练,或者和一千个流浪剑士轮流对练。他负责战舰的修整,简朴、整洁,严厉,没有不良嗜好……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家伙,惧怕他,提防他。他很杰出,也很孤独,更没有朋友。
每当吴王举办水上宴会,为防止暗杀,总是随机选择船只。事发当晚,恰好选择了余桥棠下的舰艇,结果被飞廉所刺杀。
事实上,舰长与飞廉早就开展了严酷的精神与体力的相互折磨。很多人相信,是因为他深深迷恋飞廉,他需要一个竞争对手,一个宛如朋友那样了解彼此的敌手。当时从越国俘虏来的人,一部分沦为宫廷奴隶,一部分押送太湖船场,或者赏赐给大臣贵族……至于飞廉,吴国人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置飞廉,因为越国人也没想好怎么处置他,他被遗忘在余皇大船上。中间的故事很多,以后再说。
最后一个夜晚,飞廉要余桥棠下舰长把吴王请上舰艇,“大家知道怎么投机取巧,让王来到自己管辖的船只,趁机博取赏赐和提拔,你当然也知道。”
“你有什么企图吗?”余桥棠下问。
“我的企图,不是你乐于面对的吗?”
余桥棠下接受了挑战。
于是,吴王本来要去另一艘船,却还是登上了飞廉的这一艘。
END。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八日。
第五集 越君允常及其宫廷 第四节 交叉的秘密
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交叉的秘密,这些秘密重合之处就是我们生死存亡之所。
——从南到北。
允常因为年轻而经历过一次快乐的流放。他窥视着故乡参差不齐的海岸线,它在地平线上跳跃,仿佛在向他告别。他呼喊,但没有人回答他。“我太远了,”他想,“世界听不到我了。姐姐要是知道我向世界告别时呼喊的是她,她会不会高兴?”
他从犀牛踏着细碎金光走进梦乡的南方,一直流亡到冷得让人无法呼吸的北方……漫长的航线,有人病亡,尸体被抛入万顷碧浪,就像等待失踪的航标,指示着不可见的故乡。
在银杏叶铺成的日落大道的终点,允常与伶子住到了一起,朝夕相处,他们都把对方看作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所以对彼此什么也不隐瞒。事实上,从那么远的地方乘船而来,本身就无须再保守什么秘密。他们不久陷入君臣和暗杀的漩涡,伴随以永不休止的歌唱……就像一场生与死的预演,没有人把他们记录进《春秋》或者《左传》,一切都被梳理,被淡忘,只留下《诗经》中无法署名的歌咏几行,这些小事难以公开,应当自行消亡于两个朋友之间。
——自西而东。
飞廉从秦国以西的戈壁,流浪到暴雨滂沱的入海口时,已成为一名出众的江洋大盗,一位整洁但可怕的男人,人人不是想收买他、就是杀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