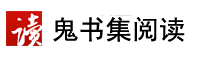第22节
因为,他忘不了每次的梦中,姑娘转身离去时的凄楚幽怨面容……她分明是在怨我呀!老根叔每次都在梦中哭醒,复仇的信念更加坚定。
“杉杉,虽然我不知是谁害了你,但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你们家仇人中的一个,我不会放过他的,你一定要保佑我……”此时,老根叔喃喃自语着。
可究竟该怎样惩治这个“仇人”呢?老根叔还没有想好,但不管怎么说,先试探试探他还是应该的。
第二天一早,家家户户的牛群刚刚出村,老根叔照样又转悠到了满仓家门前,照样看到铁生坐在自家墙根底下抽着闷烟。铁生抽烟时面无表情,烟雾飘过他的脸面,使他看上去就像一尊香火烟气笼罩着的泥塑神像。铁生旁边倚着窗台斜杵着的,是他那支从不离身的拐杖。由于太长的使用年限,拐杖靠近咯吱窝和手摩擦的地方已被磨损得铮亮,在渐渐明亮起的深秋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芒。
老根叔装作全忘了昨天的争吵似的过去跟他打了声招呼,然后一屁股坐在昨天坐过的地方,掏出早已卷好的烟卷递过去。
铁生看了一眼老根叔递过来的旱烟卷,没有接,却伸手慢腾腾地在自己身上摸出一个烟盒,打开盖,熟练地弹出一支点上。看得出,他还在生老根叔昨天的气。
装个鸟球!老根叔斜眼看着铁生的一连串动作,心里骂着,脸上却显出不在意的样子笑呵呵地道:“到底是坐过官的人,不一样啊!可是在场部住久了,这仓库也能住得习惯?”
“这是我儿子的家,有什么住不惯的?再说,这家修整成这样,估计也没几人能比得上吧?”铁生并不看老根叔,他慢悠悠地吐出一串烟圈,一脸的傲气和无所谓。
瞧那样子就不像什么好人!老根叔在心里骂道。脸上却依旧笑着,他有意干咳了两声后,接着铁生的话说:“是啊,是你儿子的家,可也是那女鬼的家啊!你真的不害怕?”
铁生扭头看了老根叔一眼,有些蔑视地说:“那些无……”别看铁生当过兵、做过干部,可那全是凭的蛮劲儿,其实他骨子里就是个大老粗。此时,他本想说的是“无稽之谈”,可“无”了半天,也没想起这四个字是该怎样说的来,只好改成“那些别人胡说八道的事,你也信?”那意思是说,你也太没文化了吧?
老根叔当然听得出铁生的话外之音,可他并不在意。他的目的不是和铁生打嘴仗,而是要把恐惧的种子播撒在铁生的骨子里。于是他说:“可是这里真的有过女鬼哭嘞,还有那些怪事,你难道一点不纳闷?”
铁生仍然坚持着他的无神论,可又没有更好的语言来反驳老根叔,便反问:“哪来的女鬼,什么来历,姓什么?你若说出来我便信你,若说不出来,就甭再提!”
“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仓库里过去好像住过一家姓赵的人家。后来不知怎么回事,这家的人死的死、散的散、失踪的失踪,其中的一个姑娘据说还怀孕了。大概,这个姑娘就是现在这个女鬼吧?”
老根叔的话说得轻飘飘的,可飘到铁生那却变成了冰冷冰冷的雨,就像他脊背上突然冒出的冷汗。“姓赵,一个姑娘?”他看着老根叔,眼睛瞪得老大,刚才的傲慢和不屑登时消失得一干二净。
“是啊!对了,好像还说和什么兵团的什么人有关系!”老根叔故意一惊一乍的说着,同时用余光观察着铁生的反应,“听人说,是兵团的一个年轻人让那姑娘怀了孩子,可随后又抛弃了她。女孩儿的家人写了上告信,却被那年轻人的一个领导,可能是连长吧把信给截了下来……”老根叔说到这儿,像想起什么了似的问铁生,“对了,你那时不是连长吗?这个缺德的连长,该不会——是你吧?”
老根叔的问话没有得到铁生的任何应答,这倒不是因为心安镇定,而是突然而至惊慌恐惧,让铁生已经完全惊呆了!
老根叔当然想象得出铁生的反应,他解恨地回头看了铁生一眼,像看到了一具没有思维的木头人。
老东西,害怕了吧?这叫自作孽不可活!等着吧,这才刚刚开始,好戏还在后头哪!
老根叔在心里恨恨地说着,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了。
老根叔走的时候,铁生还雕塑一般坐在那里,将至中午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明晃晃的。这让老根叔更加觉得有些恶心,因为他感到,阳光下的铁生,五官变得更加清晰地丑陋着。
第七十二章 夜半的叹息
铁生坐在屋外窗台下发呆了很久,直到铁嫂喊他进屋吃饭他才发现太阳已上杆头了。
进屋后的铁生开始心事重重、闷闷不乐。饭桌上,沉默了许久的他突然开口对满仓说:“明天我和你妈带着宽宽就回去了。”
“为什么?”父亲的话有些出乎满仓的意料,他不解地看着父亲问,“您不是不想走吗,那就多住几天嘛,反正宽宽现在是休学养病,回去也没什么事。再说,您不是说要在这儿等小涛回来的吗?”
满仓的话没错,铁生本来是想住在这儿等小涛回来的,可现在,老根叔的话,让他对这个仓库改成的家产生了恐惧。在这之前,他自己实在没想到自己过去的那段有悖于良心的不光彩历史,会与这个仓库联系在一起。一想到这儿曾经住过那个被自己间接害死的姑娘,他的浑身就一阵阵发冷。他甚至想到了秀秀的死,并把秀秀的死归咎为这个仓库的不吉利和那个含恨而死的姑娘的冤魂的复仇。所以,他要尽快离开!
可铁生不想说出自己真正要离开的原因,因为那是他自己心里藏着的鬼,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于是,他怏怏地问满仓:“前些日子你不是还劝我回去的吗,怎么现在又变卦了?”
“因为我要出去寻找小涛,需要您在这里给我看家。”
小涛出走六天了,当地警方仍是毫无线索。满仓无奈,心想村里的牧草已收得差不多了,也没别的大事了,不如自己出去亲自寻找小涛吧。可自从上次在老根叔家发现了红、黑两种油漆桶外,满仓心里一直对老根叔若有若无地存在着余悸和戒备。虽然两桶油漆并不能说明什么,但凑巧的事,总会让人浮想联翩。所以这回出去寻找小涛,他准备不再找老根叔为自己看家,可实在又找不出像老根叔这样的闲人,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请父亲留下来等他回来。
听了满仓的话,铁生尽管一百个不愿意,但又没有拒绝的理由,只好勉强答应。
满仓临出发的头两天,买回了两部手机。一部自己留着,一部交给了父亲,说联系起来更方便,并教会了父亲大概的使用方法。
满仓走后没几天,铁嫂带着宽宽也回了场部。这是铁生的意思。
铁生虽一条腿不方便,但日常生活完全能够独立。况且满仓走后,老根叔有事没事的也经常过来坐坐,帮着忙乎忙乎。一来二去,铁生对老根叔那天说的话也不再在意。老根叔也隔三差五地拎瓶酒来,由铁嫂弄俩菜,热热乎乎地喝上两盅,越处是越投脾气。老根叔也绝对不再提那天说过的话题,这让铁生紧绷的神经渐渐地松弛下来。心情一放松,铁生就觉得铁嫂在这儿有点妨碍了他和老根叔的交往,索性让她带着宽宽走了人。
转眼,残秋被西风一扫,狐狸的尾巴样倏地无影无踪了。冬雪飘来的一天夜里,铁生把跟他喝得话扯扯话扯扯的老根叔送出门,转回屋坐在沙发上边抽烟边看电视。九点来钟的时候,困意涨潮般一波一波漫上来,冲得眼皮拼命睁也睁不开。铁生便把拐杖放在床边,脱鞋上床,头一挨枕头鼾声便雷鸣一般低一声高一声地响起。
不知睡了多久,铁生突然被一种声音惊醒。
“唉——”
仿佛是一声叹息,而且是一种女人的叹息,低沉而冗长、神秘而清晰,在寂静的夜里异常地惊悚。
铁生浑身一个激灵,却没敢动弹,而是屏住呼吸,在黑漆漆的夜幕中惊恐地睁大双眼,极尽努力地搜索着声音的来处。
“唉——”又是一声,像是来自厨房,又像是来自窗外,又像是来自身边。
“谁?”铁生吓坏了,抗美援朝渡过江,开垦荒原打过狼的他,此时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在下一个叹息声刚刚响起之时,惊惧地发出一声惊颤的喝问后,倏地用被子紧紧蒙住了头。
叹息声嘎然而止,再没有出现。可不久,一阵女人的哭声却隐隐约约由远而近地传来。
很快,哭声似乎在门口停住了,门窗突然像被风吹得哗啦哗啦直响。这平静的天哪来的风啊?铁生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地想着,却听见一个女子啜泣的声音在叫:“爸,妈,开门,开门啊!”
铁生想到老根叔说的女鬼,肩头突然一松,一泡尿吓得撒了出去。他既害怕,又委屈,第一次孩子般地压抑着嘤嘤地哭起来。
许是女鬼听到了铁生的哭泣声,叫门声停止了。女鬼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了句:“啊,走错门了啊。”接着,门窗不再哗啦哗啦山响,倒是隔壁半拉仓库门突然吱呀一响,又哐地一声,仿佛有人进去后,又把门紧紧地关上了。
铁生听着这一切发生,一直躲在被他尿骚的湿被窝不敢动弹。看样子,这间仓库闹鬼是真的了。大半辈子都不相信鬼神之说的铁生此时也不得不这样想了。
那么这女鬼到底是谁呢?铁生想到老根叔说的几十年前曾经住在这里的一家人,想到自己曾经对这一家人的伤害,心里越加害怕。他猜想着,是不是女鬼知道了自己独自住在这里,故意来找自己寻仇?转念又一想,不一定,刚才女鬼不是自言自语地说走错门了吗?这说明女鬼并不知道自己住在这里。这样想着,铁生的心又稍稍宽敞了许多。
鸡叫头遍的时候,天开始了蒙蒙亮。铁生的困意再次袭来。他听人说过,再厉的鬼也会在鸡叫之前离开的,便心里没有了负担,也不顾了被窝里的潮湿,开始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
明天一定给满仓打个电话。进入梦乡前,他这样嘱咐自己。
一切归于平静的时候,只有月亮钻出层云重新睁大了眼睛,因为它看到,一张脸,此时正贴在仓库的玻璃窗上,诡异而得意地看着浑然不觉的铁生无声地怪笑着……
第七十三章 诡异的电话
连续两天飘来的小雪并没有稳稳地站住脚,而是被还有些温吞的江风一吹,在地面上形成了一小层薄薄的冰,在雪过天晴后的阳光的照耀下,隐约地闪烁着莹莹晃晃的七色之光。
因为太滑,路上来往的行人不得不放慢了脚步,就连每天太阳还没露脸就已在村里嘚嘚跑着按喇叭的收奶车,今天也姗姗来迟。
这一天,牛村的节奏仿佛一下子缓慢了下来。
可此时,一个身影却从村口处焦急而来。身影一下一下侧歪着,走到近处,才看出是一只单拐和一条好腿交替挪动的结果。由于欲速不达,来人焦虑的脸上和额头已经渗出了密集的汗珠,在阳光下随着脚下的一跛一跛而一下一下地闪着亮光。
来人正是满仓的父亲铁生。此时,他无视于不断遇到的行人,无视于脚下的路况,就像一只咬败了架急着去搬救兵的野兽,气急败坏地向老根叔家走去。
铁生好不容易挪到老根叔家时,老根叔正坐在外屋地抱着一张铁皮叮叮当当地砸着。看到铁生,很诧异,问:“这刺溜滑的天,你怎么跑来了?”
“找你有事!”铁生闷声闷气地说着,一屁股坐在门边的一个小板凳上,气喘如牛。
“哎呀,今天孩子让我帮着砸两个奶桶,就没过去看你。你也是,有啥事打个电话不就得了,非要自己一瘸一拐地跑来。这要不小心滑一跤可咋整?”老根叔嘴上关切地说着,心里却在骂:咋不一下子摔死你个不积德的老杂种哪!
“你老东西说得怪中听,你啥时候告诉过我你家的电话号码了?”铁生忍不住回了一句,话一落地不等老根叔张口就又一本正经地转了话题,并且脸上挂着少有的紧张,“不说这些了,我来找你,可是碰到大事怪事了!”
“啥事啊,这么邪乎?”能从铁生脸上看出紧张,老根叔猜想事情一定不会小,不禁神色也跟着肃然起来。
原来,那天晚上铁生听到女鬼敲门吓得屁滚尿流后,就想着天亮后赶紧给满仓打个电话,可第二天一拨电话,没人接。再拨一遍,还是没人接。铁生感到很奇怪,担心满仓遇到了什么事,不放心,就一遍一遍地拨,结果拨了一整天,满仓的手机不是没人接就是提示正在通话中。铁生更加纳闷,晚饭后就接着拨。结果,天很黑了的时候,不,确切地说,应该是夜半深更的时候,电话终于通了。铁生倏地松了一口气,悬着的一颗心像太阳落尽了大海里一般一下子落在了肚子里。他刚要开口训儿子几句,电话那头却先传来了声音:
“爸——”声音沙哑而低沉,在寂静的黑夜里,仿佛从阴冷的地下传来。
铁生一惊,虽然对方喊自己爸爸,可听声音分明不是自己的儿子呀!
铁生沦陷在疑惑和惊恐中还没醒过神来,对方又说:“爸,我是您儿子满仓,我现在已经不是人,而是一个孤魂野鬼了。我是被人勒死的,所以您听不出了我的声音。爸,我死得好冤,您一定要找出凶手,替我报仇,否则我死不瞑目,死不瞑目啊!”说着,声音像随着什么飘走了似的,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一丝呜咽,和风搅在了一起。
铁生一直是呆愣愣的,整个过程,他一直手持电话,嘴张得老大地听着,直到电话中只剩下了滴滴的忙音,他才反应过来重新拨通电话大喊:“满仓,满仓啊,你这是咋的啦,你快回来,回来呀——”
“嘿嘿,你儿子已经走了,他回不去了。唉——”电话中,突然传来一个女人诡异的冷笑和尖细的声音,尤其那声“唉”,让铁生陡然想起了那个夜晚那声女人的叹息声,他不仅手一哆嗦,电话重重地掉在地上,发出了滴滴的声响。
半天,铁生才战战兢兢地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时针正好指向十二点。这正是传说中鬼魂出没的时辰。想到这,恐惧、无助、伤心立马像三根拧在一起的绳子,紧紧地捆绑住了他,令他瞬间有了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他软软地从床上出溜到了地上,有生以来第一次泪流满面,压抑地大放着悲声。
铁生哭了半宿,天麻麻亮时意识才开始逐渐苏醒、逐渐清晰起来。他细细地回想了昨晚整个事情的所有细节,想,一般冤死的鬼魂,都是托梦才对,没听说过鬼魂还会打电话,这其中一定有诈。想到这儿,铁生决定早饭后便去找老根叔商量商量这事咋办,在这个村,除了老根叔,他也不认识别人了。当然,铁生是没心思吃早饭了,“早饭后”当然指的是老根叔的早饭。
老根叔听完铁生的叙述,也颇感奇怪。自己这辈子走南闯北,也算是见识不短,可这种惊悚、玄乎的事情还是第一次听说。
“你确定号码没有拨错?”他眯着阳光下一双颇显锐利的眼睛问铁生。
“没有,绝对没有!”铁生使劲礅着拐杖咬牙切齿地保证着,“不信你来拨试试看,这大白天的肯定是无法接通,或通话中,要不就是没人接。”
老根叔拿过铁生递过来的手机,按照铁生的指点小心翼翼、仔仔细细地拨出了满仓的手机号。结果情况真的和铁生说的一样,手机那头传来的果真是滴滴的占线声。
“真是奇怪了。”老根叔摆弄着手机左看右看,嘟囔着,“是不是这玩意儿出了毛病?”
“不能吧,如果是它出了毛病,应该怎么都不会通的,可晚上时它确实是通了……”铁生急急地说。
老根叔想想也是,他沉吟了半晌说,“要不然这样吧,今晚我陪你一块住在你家,半夜时再打电话,我听听到底是怎么个情况,然后咱再想办法看咋办。”
铁生无比信赖地看着老根叔点了点头,那神态,就像一个可怜巴巴的孩子。这个自以为是了大半辈子的人,现在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六神无主了,只好老根叔说啥就是啥了。
第七十四章 捉鬼的夜晚
这是一个平常得再不能平常了的夜晚。天有些阴,没有月,也没有星,整个天空就像扣在大地上的一只铁锅,倒现着黑黝黝的锅底。
此时,在满仓仓库的家里,铁生和老根叔正对头躺在一张床上,望着墙上的挂钟的钟点无声地等待着。
时间,在挂钟哒哒的响声中流逝着,像一片水在慢慢流淌。不知何时,外面似乎有了一点风声。风不知打在什么上,当当的,像是谁的手在轻轻敲击窗棂。
铁生和老根叔仿佛约好了似的一骨碌坐起来,同时向窗户的方向望去:那里,黑洞洞的,什么也没有。
是风哦。两人心里同时说着,不约而同地对望了一眼,然后迟疑地重新躺下。
许是风声衬托的缘故,屋里越发显得异常的安静,静得仿佛彼此都听得见对方的心跳。
墙上的挂钟当当地响了十二下的时候,铁生战战兢兢地掏出手机,仔仔细细地拨出了满仓的手机号,然后哆哆嗦嗦地把手机递给老根叔:“你听吧。”
老根叔接过手机贴在耳朵上,里面滴滴几声长音后,果然一个嘶哑得可怕、阴沉得瘆人的声音传了过来:“爸,我好疼好闷啊,我现在就在一间被水泥压住的屋子里。我的尸体正被一群野狗撕咬,您快来救救我吧,别让我死了连尸首都回不去,回不去呀……”老根叔的头皮开始过电般麻嗖嗖起来,长这么大,他还是头一回遇到这事,不免也有些心惊肉跳。但短暂的恐慌后,他还是稳住了心神,冲着话筒破口大骂起来:
“你到底是谁?有种的出来,不用装鬼弄神的吓唬人,老子不怕你!……”
正所谓,“厉鬼怕恶人”。老根叔的一通咆哮怒骂,让电话里的声音突然消失了。老根叔喂喂地对着里面喊了几声,见没有回音,刚要放下手机,一个尖厉的猫头鹰冷笑般的声音却猛然在他耳边炸起:“老不死的,你儿子的命我收了,你是要不回去的了。我告诉你,你害得我做了孤魂野鬼,我迟早也会收了你的……”说着,声音渐渐变小,似乎一路阴笑着走了,任老根叔怎么喊怎么骂都再无声音。
“你害过人?”老根叔放下手机,一头冷汗地扭头望向铁生,却发现铁生两眼直勾勾地望向门口一动不动,脸上的表情是诧异还是惊恐难以描述。
老根叔顺着铁生的目光望去,不由也倒吸了一口凉气:透过敞开的卧室门,他看到,正对着卧室的客厅大门不知什么时候四敞大开了!
这?那明明是上了锁的呀!
老根叔犹豫了片刻,突然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谁?”他大喝一声,一个箭步冲到大门外。可门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轮不知何时出现的冷月正在风的助力下透过厚厚的云层露出半张惨白的脸,在陈旧的仓库上空显得愈加清冷,仿佛一只诡秘、挑剔的眼睛在冷冷地看着他,讥笑着他。
老根叔重新朝四处看了看,在确定真的没有什么异常时,才重新关好门,上好锁,然后向卧室走去,边走边奇怪地琢磨着,不知琢磨到了那一块儿,嘴上突然冒出一句:“难道除了我,还会有别人?”
“什么除了你还会有别人?”老根叔说者无心,铁生却听者有意,他本来一直呆呆地坐在床上,虽看着老根叔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思维却无法聚拢,脑袋里空空一片。可老根叔的这句话却仿佛一个鼓槌,一下敲醒了他,他觉得奇怪,不知老根叔为何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铁生的突然发问,让老根叔愣怔了一下子。他下意识地抬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嘴巴,解释说:“哦,没什么,我的意思是说难道真有比我还胆大的鬼么?”
“哦。”铁生答应了一声后,思想马上从刚才的呆傻和混沌中回到了眼前的恐惧和悲伤里。想到刚才手机里传出的鬼话,他几乎孩子般带着哭腔问老根叔,“怎么办呢?满仓是不是真的死了?”
“不会……吧!”老根叔本来想干脆利落地回答个“不会”,可突然间想到铁生就是自己寻找了二、三十年的“仇人”,看到他担心难受痛苦悲伤的样子,自己真是觉得很快意,便马上改了口,多出了个犹犹豫豫的“吧”。
铁生当然从老根叔的口气中闻出了不祥的气味儿,他低下头,沉默片刻,终于还是忍不住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明天去找站长助理。”欣赏够了铁生的落魄样后,老根叔又向铁生抛出了一线希望,“听说站长助理学识渊博,肯定比咱俩见多识广,知道的事也多。”
老根叔的话宛如一只强心剂,让铁生渐渐恢复了正常的心跳,最后终于抵不住疲惫的煎熬昏昏睡去。
当铁生的情绪正趋于平静的时候,老根叔却躺在床的那一头毫无睡意。他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苦苦地思索着刚才发生的一切——